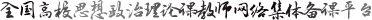摘 要:1908 年的霍乱是目前可查晚清渝城发生的第一次烈性传染病,引起了地方的广泛关注。试图摆脱“地方性事件”的解 释框架,将此次大疫置于晚清中国大变迁的背景以及重庆———中国内陆开埠城市的特征中思考,希冀通过细腻考察 各方力量对这起霍乱的态度以及采取的应对措施,勾勒出晚清重庆城地方权力的运作以及西方殖民势力的影响,进 而展示这座开埠口岸复杂的社会生态,以深化对近代重庆城市以及晚清中外关系问题的理解。
“霍乱”一词,在中国古籍中出现极早,并不是 近代的舶来品。《灵枢·五乱》篇就有载 : “乱于肠 胃,则为霍乱”。 [1]248名医张仲景在《伤寒论》中也谈 到,“病发热头痛,身疼恶寒,吐利者,此属何病? 答 曰:此名霍乱。霍乱自吐下,又利止,复更发热 也” [2]1132 。中国早期文献中所载的“霍乱”,多指胃 肠炎一类的疾病[3]28,与今日所指的烈性传染病有 所不同。现今意涵上的霍乱( Cholera) 主要指由霍 乱弧菌引起的急性消化道传染病。 [4]109目前的研究 多认定是在清嘉庆年间,经海路由印度半岛传入中 国。 ①此后很快成为对国人生命健康产生极大威胁 的烈性传染病。 目前关于清代霍乱的研究,多见于北京、天津、 上海、江浙等地②,关于内陆腹地的发生情况较少考 察。以上地区的关注和探讨自有其重要意义,然而 学术研究不可能仅停留在一定的地方或区域。笔者 通过对“巴县档案”的爬梳,发现 1908 年重庆城发 生了一起牵动各方关注的霍乱症,且隐含了丰富的 文化意义,为相关问题的探讨提供了可能。因此,本 文以此则档案史料为文本,再钩沉其他有关文献,围 绕这一议题展开多角度的探讨,不当之处,敬祈各位 方家斧正!
一、 1908 年的霍乱与地方政府之互动 1908 年渝城的霍乱症,从衙门的告示中知晓传 染源并不在本地 : “照得下河一带,现有时疫流行, 渐渐传入县境” [5] 。据此,可大胆推测概因川江上 人员的跨区域流动导致爆发于长江中下游地区的疫 症逐渐传入了重庆境内。至于具体是什么地方? 经 进一步考察发现,极有可能是汉口。 英国记者丁乐梅在20 世纪初曾往西部游历,途 径湖北汉口时,在游记中留下这样一段文字 : “在 1908 年夏天,不下28 个外国人死于霍乱,当地人的 死亡数量更是不计其数。” [6]9丁乐梅留下的记载中 强调的时间和季节都与档案反映的情况基本吻合。 故而笔者推测此次霍乱极有可能是由汉口传入渝城 境内的。这当然是与重庆坐拥两江,水上交通运输 网发达的因素休戚相关。尤其是到了近代,随着交 通运输业的发展,在打破区域间的地理阻隔,沟通各 方人员往来的同时,也导致了各种传染病的跨区域 流行。所以说,便利的川江航运,给重庆带来商贸发 展机会,也带来了疾病的危害。 “档案”关于此次疫情的应对办法记载较为详 细,从中可窥见,为了预防此次疫症的蔓延、扩散以 及医治感染人群,各级地方政府的长官果断采取了 一系列称之为积极的应对措施,概括起来主要包括 以下三个方面。 ( 一) 检查船只,遮断交通 作为一种烈性的肠道传染病,得此病者顷刻毙 命,异常危险。学者张大庆统计1840—1911 年对中 国生命健康威胁最大的烈性传染病,霍乱高居榜首, 流行频度达 45 次,平均 1. 5 年就有一次,其次才是 鼠疫、天花等。 [7]19极大的“杀伤性”和“高死亡率”是 霍乱的主要特征。西方学者研究 19 世纪直布罗陀 霍乱症时,也指出,“作为臭名昭著的最致命的传染 病之一,剧烈的呕吐和腹泻快速脱水致使一个人在 数小时内毙命” [8]96 。疫症发生不久,巴县衙门就派 出差役等人员到境内各处不时巡逻查看,发现异常, 立刻上报,以便对疫情进行防控。为了阻止传染源 的扩散,保障渝城百姓生命健康,川东道台下发札 文,要求县衙即刻派人到大佛寺的下游设置排查点, 检查过往的船只是否载有患病的人员以及因此病故 之人。若有,“务令其即在下游起岸”,不准其继续 上溯,更加不准上岸,以此减少危害程度。 [5] 大佛寺筑于重庆最早的水运码头———弹子石 上。而弹子石位于两江交汇之处的南岸,与朝天门 隔江相望,有大量人员会由此进入重庆城。所以,此 处设防可以限制病源携带者的活动范围,防止祸延 多地。 本年刚赴任的巴县知县吴以刚接到道台的文札 后,即刻责令衙门差役到大佛寺附近检查来往船只 情况。同时,吴知县明令 : “上下游来往船只内,如 有患疫病人,不准靠泊码头,以免传染,如违重究不 贷。” [5]值得注意的是,以上对来往船只人员检查以 及水路交通线一定程度上的封锁行为,实际隐含了 检疫隔离制度的影子。当然不能藉此推断重庆已引 介并推行了具有“近代”特征的检疫隔离制度。一 般而言,此类活动的开展,都会由“隔离所”“检疫 所”类似的机构组织来负责。如时论言 : “防疫一事 本为卫生起见,例在口岸设一验疫所,以防传 染”。 [9]5496从档案反映的情况来看,当时的重庆并无 此类机构,而地方政府的做法,应该是属于传统的避 疫手段,尚不涉及检疫这一近代的卫生制度。不过, 通过这一举措可作进一步思考的是,所谓的“近代 化”并不一定都是西方文明带来的,也可能是中国 在积累到一定程度后形成的。 就本例而言,可以想象人们一旦意识到此种方 式的有效性,极有可能会逐渐推广并形成近代意义上的卫生检疫制度。况且,近代中西接触、交往,是 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并不存在一种文明的进步全 由他国文明引导。梁其姿教授甚至有谈到,“许多 被认为具备‘近代’特色的制度、态度其实早在前近 代的中国就已出现”。 [10]120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渝城作为西部商业中心, 与外部世界的经济交往十分依赖长江这条“黄金水 道”,为了防止时疫的蔓延,通过行政力量强制阻隔 交通、限制人员往来的做法,无疑对本地经济发展有 阻碍影响。尽管在档案中并未有相关内容的体现, 我们却可以臆测针对地方政府的强制行为,极可能 引发渝城及外地商贩的抵触情绪,政策是否得以很 好落实,值得商榷。 ( 二) 设局延医,医治病患 鉴于南岸王家沱地方已有不少百姓感染,除去 预防措施采取外,治疗活动更是不可或缺、紧迫的。 作为六品的江北厅同知郭钟美建议在疫情预防的基 础上,更宜考虑“治疫之方略”,为此采取了在警察 分局下面成立防疫卫生局的办法,试图通过专门的 机构做到有组织、有计划地对患病轻者进行诊治救 护。 [5]仔细考量这一新式机构,实则为清末新政的 革新影响。 清末国家内外交困,中央政权摇摇欲坠,时人指 出,“欲救中国残局,惟有变西法一策”。 [11]8527 1901 年1 月 29 日,清廷发布改革上谕,标志新政的启 动———“世有万古不易之常经,无一成不变之治法。 穷变通久见于大易,损益可知著于论语。盖不易者 三纲五常,昭如日星之照世; 而可变者令甲令乙,不 妨如琴瑟之改弦。” [12]460这一场改革几乎涵盖社会 各个领域,包括医疗卫生尤其在卫生机构设置方面。 光绪三十一年( 1905) 朝廷谕令京师及各省一体举 办巡警部。巡警部内设有五司十六科,其中卫生一 科“掌考核医学堂之设置、医生之考验给凭,并清 道、检疫计划及审定一切卫生保健章程” [13]。“三 十二年改巡警部为民政部”下辖“一卫生司,掌核办 防疫、卫生、检查、医药、设置病院。……原设之警保 司卫生科事务并归办理” [14]8791 。毫无疑问,国家从 制度建构层面确立的医疗卫生机制,会对地方相关 组织建立起到推动作用。渝城设立的防疫卫生局正 是晚清中国在医疗卫生领域变迁的体现。 渝城设立防疫卫生局,“添延医士”多名,聘请 有专业知识的人来主持医疗活动的开展,并且拟定 章程六条,以实现医疗机构的规范化运转。 [5]档案中还较为详细地说明了防疫卫生局设立在选址上的 周全考虑:一是选择新城“地广人稀,空气较好” [5] 的地带。这主要关系到空气与疾病关系的问题。人 烟稠密之区,不仅不利于病症的医治,还容易滋生瘟 疫。比如,有论断曰 : “人聚一处,易染急疫” [15]244 。 鉴于霍乱极强的传染性,地方政府在卫生局的选址 上,尤其注意选择人烟稀少之处,从而可以阻滞疫情 的蔓延,以减少人群的感染。此外,“空气较好”,多 指其清新与流通的畅达。王有性在《随息居霍乱 论》就强调,“霍乱痧胀,流行成疫,皆热气病气,酝 酿使然。故房中人勿太多,门窗勿闭,得气有所泄 也”。 [16]20二是所选地址必须与官署相近。毗邻官 署,可预防“照料无人”等问题的出现,这就利于对 病情随时观察以及病患的医治。不论是从“防”还 是从“治”的角度来看,倡议设立的卫生机构可谓良 苦用心。 渝城成立的防疫卫生局是近代重庆城市发展中 的重大事件,如伍连德所说,“我国往时疫病流行, 从未闻有防御之者,该次实为中国举办防疫之起点, 树公共卫生之基础,厥功甚伟” [17] 。 此外,“防疫卫生局”这一专门机构的设置,很 大程度上也改变了渝城传统的医疗空间。“因为中 国人自古并没有把病人委托给陌生人加以照顾的传 统,中国人的治病程序是以家庭本身为单位,病人身 体的治愈是依靠外请的医生,但护理程序的最终完 成是在家庭空间中实现的。” [18]14即传统的医疗单位 是以“私家”的形式而非“公共”的形式出现。而当 下的做法,是运用行政权力将病患“圈定”在一个特 殊的、封闭的公共的空间中医治、护理。这一变化, 体现出的是渝城简单的物理空间到复杂的社会空间 的转换———行政力量通过对民众“身体”的规训、控 制,达到集中基层权力,整肃社会秩序的目的。当 然,依靠行政权威可以调动各方力量,却不失为疾病 防、治的有效措施。 ( 三) 施银救济,全人性命 除了专门机构、组织的设立外,治疗活动的很好 开展,还不得不依赖充足的资金。政府通过经济手 段应灾是一种传统且有效的方式。比如,光绪二十 二年( 1896) 三月初六日,洪岩厢失火,延烧花户五 十六家。衙门鉴于居民惨遭回祿,无屋棲止,捐出银 两11250 文,以示赈恤。 [19]对于这次由长江下游引 起的霍乱,县令吴以刚发布晓谕称: 访得到王家沱地方,现有一种时疫……现 由本县捐钱发交该处首人,凡遇贫苦下力并无 亲属之人得染此症……一切用费皆在本县捐钱 项下动用,事后开报,倘有不敷,准首人续 领。 [5] 病患的医治、殁者的埋葬,皆需经费的支持,这 对于下力为生亦或无业游民来讲,是难以甚至不可 能负担的。正如明人林希元所述,“时际凶荒,民作 疫疠,极贫之民,一食尚艰,求医问药,于何取 给”, [20]除自生自灭外,旁无他法。清代也不例外。 这次突如其来的时疫,县衙确立了“一切用费 皆在本县捐钱项下动用”的原则,甚至指出“倘有不 敷,准首人续领”。通俗讲,相关花销不设限制。具 体操作上,先由无力医治的贫民自己提出请求,然后 再由负责地方治安的保正主持调养、医治等手续的 办理。至于费用,由保正向县衙承领,也可由保正先 自行垫付,后通过凭证随时到县衙领取。总之,衙门 主动承担了此次霍乱诊治的全部费用。 可以想象,这应该是一笔不小的开销。从正印 官的收入来看,清代巴县知县,属于正七品,年养廉 银1000 两,俸银45 两。 [21]卷6《职官》, 229与其他多数省份 比较,巴县知县的薪水是相对较低的。 ③此外,在光 绪年间,巴县衙门甚至因支出较大,不敷开支,将银 两转发殷实妥商生息,以维持日常开销的事迹。 [22] 所以说巴县衙门的财政状况并不乐观,尤其是清末 新政繁兴,更是需要消耗大量经费。难以想象的是, 在本次疫情防治中,衙门却是以一种“独占”的方式 作用其中。 除采取以上三项措施外,吴知县还将霍乱的相 关情形以白话文的形式编演成六字告示,下发各处 周知。内容上,包括霍乱的患病症状、应该采取的防 治举措以及百姓日常饮食、清洁卫生需要注意的事 项等等。 [5]这类通俗性的舆论宣传,不仅对于安定 百姓惊恐的情绪有积极作用,更利于卫生知识的普 及。可以肯定的是,它将以一种潜移默化的形式将 管理者的防疫观念、方式逐渐渗透到百姓的日常生 活中,对群众卫生习俗、心态意识的重塑起到一定的 作用。 概括而论,渝城的这次霍乱,牵动了从道台到府 衙、县衙、直隶厅一个地区几乎所有的行政机构,他 们在预防、施救的过程中,采取了系列应对办法。尽 管无法得知执行情况及实施效果,无疑这些措施是 利于疾疫的防治以及地方医疗防疫体系的形成。 通过对地方政府的措施作进一步思考,我们能从中窥探出一些时代特征来。我们看到地方行政权 力对地方医疗卫生的强力干预,取代了传统的寻求 与民间力量合作的方式,体现出地方行政试图将医 疗卫生制度化为衙门日常事务的趋势。 因为,一般而言,地方发生灾难,基于财力、影响 力以及儒家理念等多方面因素的思忖,行政机构往 往会借助地方绅矜、商贾等民间社会力量的参与。 长期以来,官绅合作已是一种常态。早在唐代,兖州 出现重大饥荒,知州崔立年便“富人出谷十万余石 赈饿者,所全活甚众” [23]230 。有清一代渝城亦如此。 同治九年( 1870) ,渝城太平、太安两厢发生瘟疫,死 亡甚重,当时即由巴县衙门与行帮谭福旺、马芳贵等 协同救治。 [24]相关例子不一而足。 反观此次霍乱的发生,未见任何绅、商的影踪。 所有的救助措施,基本都是由地方政府操办。首先, 经费上,“医药、掩埋、监守、巡兵、伙夫、杂役”的花 费全部都是由地方政府承担。衙门凭借“一己之 力”负担起一切相关开销支出,不曾动员其他社会 力量参与其中。这同前面提及的官绅合作方式完全 不同。其次,机构建制上,也并未出现往常整合社会 力量,号召绅商设立相关救助组织的情况。 ④而是在 作为行政机构的警察分局下附设防疫卫生局,进行 疫情的防控。 这一变化,当是与清末中国社会变迁的大背景 息息相关的———为了维持地方秩序,出现国家行政 权力不断下渗和扩张的趋势。此外,尤其需要指出 的是,重庆作为近代的开埠城市,西方势力是不能轻 忽的存在,在本处疫症中扮演了异常活跃的角色,值 得高度关注。 二、西力的挑战与合作 前文亦谈及重庆城“水陆交冲,地当孔道,巨商 大股,较省城尤为繁盛” [25],尤其是“随着 16 至 19 世纪中国全国市场规模以及内河与沿海航运路线的 日渐扩大,长江上游地区更大程度地被长程贸易网 络所卷入”,“重庆的商贸中心地位日渐显著”。 [26]317 因此,在近代西力对外扩张、殖民的进程中,重庆很 快成为了西方列强竞相逐利的场域。 晚清以降,西方的探险家、传教士、商人等身份 各异之人不辞万险纷纷来到长江上游及重庆,或游 历,或考察,或搜罗情报,不同程度地服务于本国的 对外扩张政策。英国人更是依凭光绪二年的《烟台 条约》率先取得了“派员驻寓查看川省英商事宜”的 特权[27]。1890 年3 月 31 日,中英两国签订《烟台条约续增专条》,规定“重庆即准作为通商口岸无 异” [21]卷16《交涉》, 502。1891 年 3 月 1 日,重庆海关成 立,重庆正式开埠。重庆成为了英国在中国获得的 第20 个通商口岸,被英国人认为是“位于中国最富 庶和最有利可图的地区之一的口岸” [28]410 。1894 年,日本发动侵略中国的甲午战争,强迫大清签订 《马关条约》,重庆成为中日马关谈判中,日本得到 的第一个通商口岸。 [29]308 “均照向开通商海口或向 开内地镇市章程一体办理,应得优例及利益等,亦当 一律享受”。 [30]151通过《马关条约》,日本和英帝国一 样,取得了开埠重庆的特权。得益于“一体均沾”的 原则,各国领事纷纷东来,后经勘定重庆南岸王家沱 为租界地。 [21]卷16《交涉》, 506重庆华洋萃集的城市面貌由 此形成。历史的吊诡之处就在于,此次疾疫流行之 处即为王家沱地区。 巴县知县吴以刚发布的告示清楚表明,“重庆 南岸王家沱地方时疫流行”,“其病状或呕、或泄、或 两脚发麻”,“异常危险”,“居民连日染患时症,死去 已有七人” [5] 。作为租界所在地,毋庸置疑,西方各 国必然对此投以高度的关注! 当疫情出现时,法国领事就派本国檏医士,且邀 德国的阿医士协同前往王家沱进行实地查考。凭借 专业的医学知识,两人得出了一致的意见,确认本次 时疫为霍乱症,“传染易滋、危险万状”,立马向领事 汇报了详请。 [5]值得一提的是,邀约阿医士之举,概 因德国对霍乱的认知和防治在当时世界上尤其深 刻。德国人罗伯特·科赫在19 世纪八九十年代,第 一次发现了霍乱弧菌,并第一次提出了霍乱预防法, 成为病原细菌学奠基人并摘获了诺贝尔生理学及医 学奖。 [31] 各国领事得知这一讯息后,纷纷向负责守城之 官的川东道台致函,要求设法预防和医治。兹摘引 法国领事白达致川东道函如下: 檏医官暨德国阿医士同往考查,确系霍乱 症。地方不知此病危险,□死去后未掩埋,亦多 施治□瘟之法,将来恐不免蔓延……窃查霍乱 症亦名“麻脚瘟”,传染极快,异常危险。敝国 人于此症查验极严,诚以一经感受,虽有灵药亦 难□功。……敝国兵船亦防备周密,绝不虑其 传染。惟念该地居民无知,而罹此灾情殊可悯、 可亲,仰贵监督慈祥恺悌、胞与为怀、布陈所知, 可否转饬地方速照以上所列之法施治,使其不 能传染,消患□形,则贵监督之迭□□民容有涯涘。查时疫流传为患□烈,故各国于防疫之法 皆极其备求。现王家沱地方既有此项时疫,应 该新执事派人劝谕民间,俾设法预防,以免传染 □□。 特此敬请 升安不具 名正具[5] 与此同时,川东道的陈道员又收到了来自各国 在渝的领事代表———英国领事费理伯的致函,费理 伯函称: 今岁天时不正,疫疠流行,一经传染,颇难 救治,是以泰西各国重视此症,如临大敌。今重 庆为通商巨埠,人民虽多,知识未开,……此症 传染,中医束手无策,徒令死亡相继,贻害地方, 一时不能净尽。敝领事忝居领袖,为各领事代 表,现已商请本国樊医士预筹防治之法,列单进 呈。请烦贵监督出示晓谕……务须严防疫症, 勿使传染,并广布治法,以期人寿同登,地方安 靖。 [5] 由上可见,两份“致函”表达意思相同: 第一,强 调此症危险万分,稍不注意即死亡相继,要求地方政 府加强管理;第二,西方各国对此疫的防治十分有经 验,出于对渝城百姓可悯、可亲的考量,提供了防治 方案,要求地方按照他们的办法开展施救活动。 倘若我们就文字表面所呈现的信息来理解,无 疑体现了西方“人道主义”精神。鉴于重庆目前的 医疗水平无法治愈,各国又对渝城人民怀有同情之 心,因此提供具体的医治办法,转交重庆地方政府照 办,以图实现“人寿同登、地方安靖”的目的。然而, 当我们从一个大的历史观,或者说结合时代背景分 析,不难发觉,西人的言行实则包含了在知识领域对 中国的挑战以及西方殖民主义的色彩。 自1840 年大清国门被西方坚船利炮打开后,王 朝逐步经受了西方文明方方面面的挑战,从军事机 制到国家政体,再到文化层面,中国的医学也未能获 免。丁福保在《历代医学书目》序中喟叹,“西人东 渐,余波撼荡,侵及医林,此又神农以后四千年未有 之奇变也” [32]249 。在近代,西人对中医的偏见言论 十分常见。 莫理循曾讽刺 : “没有哪个英国医生比得上中 国医生的从容自信,他们凭着这种自信,诊断他们并 不明白的各种病症。当中国医生把他并不了解的草
药放进他更不了解的人体内时,如果看到不幸的后 果,也并不比他的西方同行遇到同样情景更加惊慌 失措,他抽身而退,言简意赅地总评道‘须知医之与 药,只可治病,不可治命也’。” [33]161再如,英国人丁 乐梅也对中国的医学嗤之以鼻,“蹒跚而行的老中 医仍然继续着他那邪恶的营生,毒害着容易受骗的 人们”。 [6]51 就此事件而言,西方领事笃定“地方( 重庆) 不 知此病危险”,“亦无多施治此瘟之法”。各国驻渝 领事官代表费理伯为了说服重庆地方政府采纳自己 的意见,在行文中直白地表达出西方防治此症的信 心与能力,“敝国人于此症查验极严”“各国于防疫 之法皆极”“敝国兵船亦防备周密,绝不虑其传 染”。 [5] 渝城作为华洋杂居,霍乱又是传染性极强的疾 疫,洋人的“绝不虑其传染”未免有自大之嫌? 西方 膨胀的自信以及对中医治疗能力的质疑和否定,尤 其是武断地认为,“中医束手无策”,“徒令死亡相 继”的论断,充分显示出的是西方医学的霸权主义 倾向。当然,这种“医学霸权”的态度以及中西医二 元对立的论述,与西方医学在病因解释、病疫防治技 术的发展密切关系。16、 17 世纪时以解剖学、病理 学为基础的西方医疗技术获得了较快发展, 17 世纪 甚至被视作西方医学的革命世纪。 [34]72 -74到19 世纪 更是取得长足发展。在1883 年之前,西欧国家已经 建立了行之有效的传染病防治机制,并基本控制住 霍乱的大规模暴发。 [35] 据此,可以结论,近代西方的医学支撑着西人在 华人面前的强烈优越感。这从技术层面看,是西医 对中医的歧视与偏见,而“中医偏见、歧视”背后折 射出的更深层次的是“种族偏见”“种族歧视”。已 有部分研究成果对“种族歧视”问题进行了论说,指 出近代西人认为,传染疾病暴发的根源是华人不讲 卫生,华人社会是疾病蔓延的温床。 ⑤此外,学者罗 芙芸亦曾谈及,对西方人而言,他们自信在医学理论 和疾病控制上的优越性是西方区别于东方的主要特 征。 [36]76 由此可论,西方在知识领域的优越感,种族偏见 态度,更是与其侵略扩张的殖民政策不无关系。近 代疾疫的流行并不单是关乎医疗技术本身的问题, 尤其是霍乱、天花等这类烈性传染病的发生及进一 步流行、蔓延,会严重影响一个地方的安静稳定、经 济的发展。对于在渝的西方人来讲,以上问题都是极为在意之事,尤其是经济层面的考量。 近代重庆增开为商埠,意味着被正式纳入世界 市场之中,“商品贸易发展很快,尤其是进出口贸易 的数值猛增”,“一个以重庆为中心的洋货分销网和 土货购销网开始形成”。 [37]31仅以重庆进口的洋货为 例,光绪十七年( 1891) 重庆进口洋货“按市价估算, 共约关平银一百三十七万一千二十七两” [38]第17册, 33, 第二年( 1892) ,“进口洋货按市价估算,共约关平银 五百八十二万五千四百七十四两” [38]第19册, 110,呈现 出逐年递增的态势,“迅速成为仅次于上海、天津、 汉口的第四位销售中心” [39]282由此,看到的是重庆 对国外市场的依赖,反之亦然。 因此,重庆港作为西方列强在中国西部的一个 重要转口港,是列强在华殖民网络的重要据点,重庆 的稳定和繁盛直接关系列强在华的经济利益,关系 到他们的对华殖民政策。 另外,重视渝城百姓的身体健康,也是进一步殖 民、掠夺渝城“人力资源”的体现。随着对华贸易的 深入发展,劳动力成为外国人掠夺的一个重要的、有 价值的资源。外国商业性机构在华的纷纷设立,提 出了对中国廉价劳动力的需求,西人认为“中国工 人伙多,有用之不竭之势。所得工价,实非美国工人 所能自给” [40]921 。渝城就有不少华人在外国洋行、 工厂做工的情况。 ⑥试想,霍乱在渝城的大肆蔓延, 定会引起人员逃离的情形,这样就会导致渝城经济 萧条景象的出现。故而,西人对渝城百姓生命安全 的“关心”和“重视”,笼罩在浓厚的“殖民主义”历 史语境中,打下了深深的殖民主义烙印! 考察西人采取的救治行为,是与华人政府合作 的方式展开。各国领事不仅向重庆当局提供西医的 防治方法,还将他们对霍乱的认识转换为文字,名为 《霍乱症论》,随函一并提供给川东道,要求道台出 示晓谕“转饬地方,速照以上所列之法施治,使其不 能传染”。为何西人不直接开展对华人的救治工 作? 究其缘由,文章认为主要是渝城地处西南内陆, 风气较晚开通,百姓对西方的事物普遍较为陌生,不 了解西方医术,无法信任西医,甚至对西医有恐惧、 反感。晚清重庆城各种类型的频繁的华洋冲突,中 外之间嫌隙日重,便是明证,导致西人不敢擅自行 动,开展合乎西人要求的科学的医疗活动。且充分 认识到华人百姓对“皇权”的信服,转而借助中国传 统的行政权威,以便间接地实现他们的文化霸权和 控制在渝经济利益的目的,实现进一步殖民化重庆的企图。此外,这也与西方在渝的势力不如上海、香 港等地强盛相关。 灾荒救济属于地方官的“分内”之责,也是权力 所在,洋人更是无权干涉。针对本次渝城的霍乱,面 对英国、法国等西方势力较积极且强势的介入姿态, 重庆地方政府又作何反应? 是排斥亦或不理睬? 令 我们吃惊的是,档案反映出地方行政的态度是完全 采纳了意见,认为“英领事交来预防之法,尚切实易 行”,要求下级政府照洋人提供的办法来开展施救 行动。 换言之,从地方政府的态度反映出的是西方知 识作为一种隐形的权力对近代中国的挑战与冲击是 成功的。这算得上是一个饶有趣味且值得探讨的话 题! 为什么会成功? 究竟是西方在渝势力渗透的成 果表现? 抑或重庆地方政府懂得主动利用西方医 学,以维持地方稳定的能动性特征? 窃以为,后者的 可能性更大! 一方面,晚清渝城与洋人通商数十载以来,中国 人尤其是生活在华洋杂居之地的官员更多认识到了 西方在众多领域的优势,因此不再简单地盲目扞格, 对于西方文化的“染指”,给予接受与认可; 另一方 面,清代的四川地区亦饱经动荡。同治元年石达开 入川、咸丰年间李兰起义及光绪二十七年四川的义 和团运动,都使得民众苦不堪言、社会秩序严重失 序。对地方执政者而言,社会稳定当是首要的考虑。 此时洋人的态度及行为恰好可以作为维持社会稳定 的力量加以利用。 故而,在此疫中,我们看到在洋人发起的挑战面 前,华人政府并不处于对立面,而是配合与认可的姿 态,看似不合“常规”的行为,实则蕴含了内在的逻 辑性。当然,抛开其他因素不谈,华人政府的权威加 上西方先进的医学知识,对此次霍乱的防治能起到 很好的遏制作用。 三、小 结 疾病与人类相伴随、无处不在,疾病问题“并不 只是科学可以测量的生理病变,同时也是病人体验、 科学话语、社会制度和文化观念等共同参与的文化 建构”。 [41]IV文章以清末重庆的霍乱为例,以防治措 施为切入,考察背后所隐含的政治运作、权力介入以 及中外关系等问题,进而揭示出近代中国开埠城市 的社会变迁以及复杂的社会环境等诸多方面。 经研究发现,重庆的地方行政牢牢控制住霍乱 的防治权,不再借助民间社会力量,体现出渝城地方 行政职能扩张的趋势以及医疗卫生由传统的个人行 为向公共的卫生行政转变的倾向。这与时下国家内 外交困,维护统治秩序,实现行政权力在各方面建构 的目的相关。除此之外,作为华洋杂居之地,清季重 庆城笼罩在一张复杂的中外关系网络中,面临着外 来力量的强势冲击与介入,反映出清末渝城复杂的 社会环境。当然,冲出与挑战,在一定程度上也预示 着机遇,近代西方的先进文化会对中国地方社会的 发展产生刺激与促进作用。江北厅同知郭钟美在呈 给知府的禀文中就谈到“洋人”对他们的影响,“敝 厅民牧忝司,岂能默然不动?” [5]我们看到,洋人面 对霍乱的态度、行为刺激了地方行政的竞争意识,甚 至可以说还包含了朴素的“民族意识”“自强意识”, 通过积极的介入疾病活动,彰显守土之责与权! 综上观之,本文对 1908 年重庆霍乱的关注,并 不仅在于考察地方对疾病的预防与治愈的能力,也 在于探讨晚清地方政府职能的扩张以及西力在对华 扩张进程中扮演的角色、产生的影响等近代中国面 临的重大时代问题。 [责任编辑:杨和平]
注释: ① 如罗尔纲,范行准,陈胜坤等人皆持此种观点。此外,美国学者麦克尼尔也指出,“1818 年间,正在印度北部边境打了好几仗的英国军队, 把霍乱从他们设在加尔各的指挥部带走,送给他们的尼泊尔和阿富汗敌人。更猛烈的是海路传播,船只在1820—1822 年间把霍乱传到锡 兰、印度尼西亚、东南亚大陆、中国和日本。”( [美]维廉 H. 麦克尼尔.《瘟疫与人》[M] . 余新忠等,译. 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2010 年 版,第158 页) 后来的研究者也多延续这一认识。 ② 相关论文参见余新忠《嘉道之际江南大疫的前前后后———基于近世社会变迁的考察》,《清史研究》, 2001 年第 2 期; 彭善民《公共卫生与 上海都市文明( 1898 -1949)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年版;杜丽红《近代北京疫病防治机制的演变》,《史学月刊》, 2014 年第3 期;[美]罗 芙芸《卫生的现代性:中国通商口岸卫生与疾病的含义》,向磊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 年版,等等。 ③ 直隶、湖南、甘肃和云南等省,最高可达到1200 两。山东、河南、江西、浙江、湖北、福建、广东和广西九省,甚至超过1400 两。见瞿同祖《清 代地方政府》,范忠信等译,法律出版社2003 年版,第41 页。 ④ 比如,清同治五年巴县知县黄檏委托至善堂首士代办保节堂。民国《巴县志》卷17《自治》,《中国地方志集成·四川府县志辑》第6 册,成 都:巴蜀书社1992 年版,第524 页。 ⑤ 相关研究请参见胡成《检疫、种族与租界政治———1910 年上海鼠疫病例发现后的华洋冲突》,《近代史研究》, 2007 年第4 期;崔文龙《德国 在胶澳租借地建设规划中的卫生措施以及对中国人的歧视》,《德国研究》, 2008 年第1 期。 ⑥ 此种情况的大量存在,还是诱发渝城华洋纠纷、冲突的重要因素。相关问题可参见惠科《巴县衙门与近代重庆城市社会研究( 1876— 1911) 》,西南大学2018 年博士学位论文,第61—63 页;惠科《晚清重庆华洋诉讼与地方司法初探———以巴县档案为中心的考察》,《西南 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18 年第3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