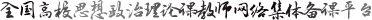摘要:
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范围内迅速扩散,一些国家为了扩大国内就业,缓解产业空心化,维护全球价值链中的“链主”地位,提出将产业链回流国内。对此,我们认为,跨国公司在中国嵌入程度高,外向配套产业齐全,相比较于“搬迁费用”,外资企业更注重产业回流后的持续运营成本,疫情不会导致外资企业大规模回流。在应对策略方面,中国应该积极打造全产业链体系,增强经济运行韧性;提升投资贸易便利化水平,降低产业链运行成本;加强应急管理,完善供应链的风险应对机制;持续推进改革,扩大开放,优化营商环境,发挥营商环境的招商、安商、稳商作用,锚定中国在国际供应链、产业链中的地位。
一、为什么会有“生产线撤离中国”的疑问?
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范围内不断扩散,世界卫生组织20日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中国以外新冠确诊病例达到2230384例。在全球供应链体系下,各国经济已经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面对全球性蔓延的新冠肺炎疫情,任何国家都不能独善其身。在这种背景下,美国、日本等一些国家提出要资助本国制造商将生产线回流国内,其原因主要在于以下几点:
第一,扩大国内就业,迎合国内选民的诉求。全球化加剧了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内部贫富差距以及收入不平衡,造成了“顶部增长”现象,10%能够参与高科技研发的劳动者收入上升,90%做中间品零部件的劳动者收入下降,就业机会减少。制造业回流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增加其国内就业,扩大政治影响力,以便赢得“铁锈带”选民的支持。
第二,缓解产业空心化,打造全产业链强国。随着制造业的不断外迁,发达国家产业空心化现象严重,中间品组装与生产多数外包给处于供应链的中下游位置的发展中国家。面对疫情的全球性爆发,全球供应链的运转步伐迟滞,高度依赖中间产品的发达国家受到强烈的“负反馈冲击”。加快制造业回流本国、重新进行产业布局,打造全产业链是有效的解决措施。
第三,遏制中国产业升级,维护自身“链主”地位。美日等国凭借其关键技术的研发优势、高效的供应链管理水平,占据了全球供应链的主导地位;而中国凭借价格低廉、资源丰富的要素禀赋位于价值链中端位置。但是,随着全球价值链体系的重构,中国正在向高端制造业升级,和发达国家不再完全是产业间的互补关系,而是直接的竞争关系。美日等国鼓励产业链回流,有助于其遏制中国的产业升级,维持自身在全球价值链中的“链主”地位。
二、美日产业为什么流向中国?
随着全球分工体系的不断发展与完善,制造行业的生产加工环节变得复杂冗长,发达国家逐步将加工、组装等低附加值环节外包给中国、越南等发展中国家。美国和日本产业流向中国的原因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资本的逐利性。企业的经济目标是通过成本最小化以实现利润最大化,资本的逐利性迫使美、日企业向外转移。一方面,美国和日本的人口老龄化严重,人口增长跟不上产业发展的要求,导致用工成本高于劳动力要素充裕的中国,将产业转移至中国可以削减劳动力成本;另一方面,加工、组装等低附加值制造业环节具有高污染性,增加了美日工业生产的环境成本,为了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美日选择将高耗能高污染的制造环节向外转移。
第二,中国产业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下,中国凭借发达的基础设施、完备的产业配套体系以及庞大的消费市场吸引了美、日企业的大规模投资。首先,中国的基础设施发达,为产业链的运作提供了良好的物流基础;其次,中国已具备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是全世界唯一能够生产联合国工业目录大类所有产品的国家,产业体系的完备性能够大幅度降低制造成本;最后,国际产业转移更注重东道国的市场消费需求,中国作为新兴工业化国家,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具有庞大的市场规模和消费潜力。
第三,中国对外开放的政策支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不断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不断优化,成为美日企业投资的主要目的地。一方面,中国对于外商投资限制和禁止产业的数量不断减少,服务业开放水平不断提升;另一方面,中国给予了外资企业包括土地使用、出口退税、企业所得税等一系列政策优惠,鼓励外商向中国国内存在短板的产业链、供应链投资,一定程度上吸引美日企业流入中国。
三、美日产业为什么不会大规模回流?
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性蔓延在对世界各国的经济造成了较大冲击,美国和日本试图实施经济刺激计划,以便将具有制造生产能力的产业回流本国。但是,从全球产业链发展的基本规律和各国区位优势的动态对比来考察,美日产业不可能大规模回流。
第一,投资信心受挫,投资者倾向采取谨慎的投资策略。疫情的爆发使得美国、日本等资本主义国家意识到全球供应链体系存在内在的脆弱性,因此想加速产业回流,建立本国全产业链。然而,产业链转移意味着扩大新增投资,这与疫情下企业保持足够的现金流,以应对经济下行和各种突发风险的习惯性做法背道而驰。特别是,随着疫情在全球范围内的扩散,不确定性因素增加,投资者信心受挫,市场的恐慌情绪会诱发投资者选择谨慎的投资策略,而不是大规模从中国撤资。
第二,持续运营成本的提高损害企业经济目标。产业选择的“磁滞现象”表明,一个地区由于某种原因,部分产业流向了其它地区,即便当该地区经济复苏,流失的产业可能也并不会回流,区域分工具有内在的稳定性。这意味着,美国和日本政府提出实施刺激计划政策鼓励产业回流,违背了产业区位选择的基本规律,难以凑效。一方面,政府补贴外资企业“搬家费用”并不具有吸引力,外资企业更注重产业回流后的持续运营成本,美国和日本高昂的人力成本、缺乏熟练的技术人才以及产业链的不完整都使得外资企业望而却步;另一方面,即使美国和日本选择产业外移至劳动力要素丰富的东南亚国家,意味着放弃现有的厂房、雇员关系以及针对中国的诸多固定投资,在一定程度上会增加外资企业的生产成本,无法实现利益最大化的经济目标。
第三,中国产业生态系统优势难以取代。全球价值链重置耗时长、难度大,不仅仅是关税成本问题,也需要考虑基础设施、供应链、配套产业的完善度等,跨国公司在中国嵌入程度高,外向配套产业齐全。与此同时,中国充足的劳动力供给、发达的基础设施和庞大的国内消费市场促使跨国企业产业链在中国聚集,是唯一能够生产联合国工业目录大类所有产品的国家。此外,中国制造在全球的份额达到30%以上,在全球制造业出口的份额大概为18%,相当于除掉中国和日本以外的整个亚洲的加总,“中国制造”的体量巨大,短期内是其他国家和地区是无法替代的。
四、中国该如何应对产业流动的趋势?
第一,打造全产业链体系,增强经济运行韧性。中国初步形成了门类齐全,体系完整的产业体系,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规定的39个工业大类,191个中类,525个小类,成为全产业链国家。面对复杂多变的全球经济形势,我们应该充分利用完整的工业体系的优势,在遭遇外部冲击后,重新整合内部资源,灵活地对经济进行调整,或扩展或收缩、利用多样化的产业结构降低脆弱性,增强中国经济运行的韧性,提高产业链的动态调整能力,做到产业链发展上不受制于人。
第二,持续推进改革,扩大开放,优化营商环境。推进“放管服”改革,实施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大幅缩减负面清单,推动现代服务业、制造业、农业全方位对外开放。全面推行审批服务“马上办、网上办、就近办、一次办”,清除利用外资中“玻璃门”“弹簧门”“旋转门”等隐性障碍,以压缩办理时间、降低收费标准为硬性指标,帮助企业降低各类交易成本。发挥营商环境的招商、安商、稳商作用,锚定在国际供应链、产业链中的地位。
第三,加强应急管理,完善供应链的风险应对机制。在全球供应链体系中,每个国家都是生产网络中的节点,面对突发风险时,完善供应链的风险应对机制无法避免。一方面,高度依赖某个中间品的供应市场在面临风险时很容易导致全球供应链的延迟或中断,跨国公司在选择生产网络布局时应注重供应市场的多样化,避免过度依赖;另一方面,全球供应链的设计应在柔性化的基础上增强链条的韧性,柔性化设计使得供应链企业在短时期内能够降低成本,但在面临高频率高强度的风险时,建设供应链预警体系,强化自身供应链的韧度才是构建供应链危机应对机制的关键因素。
第四,提升投资贸易便利化水平,降低产业链运行成本。减少进出口环节审批监管事项,简化通关程序,优化口岸通关流程和作业方式,增加海关法规和口岸管理措施的透明度;推广海关无纸化作业和全流程线上办理,自行打印海关税单,缩短增值税抵扣周期,加快企业资金流转;加快推进电子口岸建设,优化扩充国际贸易“单一窗口”标准版平台功能,充分利用互联网、物联网技术,推进口岸信息互通共享,深化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建设。通过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开创开放型经济发展新优势,留住全球供应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