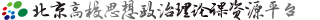[摘要]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独特民主观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民主观。在民主的本体论上,坚持现代化建设中对民主本质的践行与复归,构建了以人民为中心、以结果为导向的民主本质观;在民主的认识论上,中国式民主观形成实践性、辩证性的民主认知范式,在“两个结合”中确立适应现代化建设的民主政治发展道路,确立历史具体性的民主认知框架;在民主的方法论上,坚持系统观念和整体思维,用全过程全方位全覆盖的方法推动民主创新,开创超大规模国家的民主实践路径,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与方法论;独特民主观
[作者简介]赵春丽,北京工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北京 100048)。
[原文出处]《科学社会主义》(京),2025.3.66~74
[基金项目]本文系2023年度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独特民主观研究”(项目编号:23BKS059)的阶段性成果;北京市属高校青年人才培养计划(项目编号:BPHR202203059)阶段性成果。
习近平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独特世界观、价值观、历史观、文明观、民主观、生态观等及其伟大实践,是对世界现代化理论和实践的重大创新。”①列宁认为,“在民主的这种或那种形式上……每个民族都会有自己的特点”。②实证研究表明,东亚的民主观有其独特之处,儒家文化圈的民主观有其独特之处,中国的民主观也有其独特之处。③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独特民主观,是中国共产党在探索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过程中形成的一系列关于民主的理论、观点和看法,立足于世界现代化进程中民主发展实践与人类政治文明视野,既坚持了现代化进程中有关民主的一般原则,又有别于经典现代化理论中的民主观,在民主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层面继承、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民主观,是对中国式现代化与社会主义民主建设规律的深刻总结与阐发,集中表达为全过程人民民主理论,体现其独特性、全面性与进步性。当前学界对中国式现代化进行了跨学科与多维度的深入研究,从价值、制度、实践、话语等视角对全过程人民民主理论进行了深入阐释,就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民主观进行了相关探索。还有学者对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认识论功能、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进行了深入剖析。④总体来看,立足于中国式现代化视野的民主观研究还不够系统和深入,在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哲学高度阐释清楚中国式现代化民主观的独特性的研究不多,这为我们从民主本体论、民主认识论和民主方法论等层面研究该论题提供了探索空间。
一、民主本体论: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坚持对民主本质的复归与践行
本体论属于哲学概念,其本意是探究世界的本原与本质,即构成世界最为重要、最为核心的问题。民主本体论解答的是民主到底是什么这一问题。马克思指出,“它必须具备一定的意义,否则它就不能存在。因此全部问题就在于确定民主的真正意义。”⑤从本体论的角度来看,民主本体论追问的是民主的享有主体、服务对象以及要达成的目标等问题。民主的实质就是人民当家作主,其终极价值在于实现和维护人民的根本利益。人民当家作主要如何体现呢?一般来说,有两种较为典型的思路。一种侧重于形式和程序上的人民当家作主。这种民主观强调代议制和竞争性选举,形成了西方式排斥性—分利型的程序民主观,并且将这种形式认定为“别无选择”的“历史终结”,确立了现代化进程中的“民主一元论”和“普世论”。另一种侧重于内容和实质上的人民当家作主。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形成的全过程人民民主,强调人民在民主政治中的主体地位,从本体论层面重新定义民主的本质是人民对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全方位参与,这种理论创新既突破了西方代议制民主的抽象权利观,又超越了传统民本思想的君民二元结构,形成了中国式包容性—发展型的实质民主观。中国式现代化对民主本体论的重构,本质上是对人类政治文明形态的范式创新,这种创新在哲学层面突破了西方民主的个体主义本体论,建立了个体与集体、自由与秩序、形式与实质相统一的辩证民主观。中国式现代化确立的实质民主观,实现民主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的互促共进,实现对民主本质的践行与复归。
(一)建构了以人民为价值主体、权力主体和实践主体的民主本体论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应有之义。”⑥中国式现代化的民主观对民主本体论的建构,根植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是对马克思主义民主观的继承与发展,并实现与中华文明传统政治智慧的创造性结合与创新性发展。
马克思主义强调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民主的本质是“人民自己当家作主”,⑦中国式现代化内蕴的民主观继承并发展了这一本体论认知,确立人民作为权力主体、实践主体与价值主体的终极地位,将民主从西方政治哲学的权利让渡契约论转向实践本体论。马克思主义认为,民主的主体应该是广大人民群众,强调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明确指出,民主制的主体应该是人民,“在民主制中,国家制度本身只表现为一种规定,即人民的自我规定。在君主制中是国家制度的人民;在民主制中则是人民的国家制度”,⑧认为“不是国家制度创造人民,而是人民创造国家制度”⑨,“民主制中,国家制度、法律、国家本身,就国家是政治制度来说,都只是人民的自我规定和人民的特定内容。”⑩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民主的实质是资产阶级的民主,真正实现人民当家作主,无产阶级必须建立自己的民主统治,建立一种新的国家制度,这种国家制度要能真正表现人民的意志,实现人民的主权,确保人民既是权力来源又是治理主体。中国式现代化的民主观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主体地位的民主本体论,建立“人民”这一集体政治主体概念,承认人民才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强调广大人民群众是民主的真正主体,民主是为广大人民服务的,尽力保证人民群众能公平自由地施展他们的能力,将民主从“权力游戏规则”升华为人民的自我治理、自我提升与自我完善。习近平提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就是要体现人民意志、保障人民权益、激发人民创造活力”,(11)充分尊重人民的主体性,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释放了人民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强大的动力。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民本政治智慧,如《尚书》中“民惟邦本”“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礼记·礼运》中的“天下为公”,《孟子》中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等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为民”“信民”“爱民”“养民”等主张,亦对现代民主政治发展仍不乏启迪之意。传统民本思想虽蕴含“民惟邦本”“民贵君轻”等价值理念,但其本体论逻辑仍以“天命一君主”为终极权威,民众处于依附性地位。无论是《尚书》中“天听自我民听”的间接授权,还是儒家“仁政爱民”的道德义务,本质上都将“民”视为统治合法性的工具性载体,其福祉依赖于君主的伦理自觉,缺乏制度化权力保障。中国式现代化民主观继承了传统“以民为本”的价值内核,通过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现代政治文明的改造与融合,革除了传统民本思想中人民的消极被动和附属与工具地位,实现了从“工具性民本”到“主体性民主”的范式跃升,重构以“人民主体性”为核心的新型政治哲学范式。这种融合和改造既保持了社会主义民主的政治属性,又赋予其中华文明特有的伦理价值维度,在哲学层面构建了具有文明连续性的合法性基础。中国式现代化民主观则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理论根基,通过“人民主体论”重构政治本体,确立人民作为历史创造者与权力所有者的根本地位。这一突破体现在三个维度:其一,在存在论层面颠覆传统权力结构,以“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12)的论断将人民从政治客体升格为权力主体,在政治领域构建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体系,通过宪法确立“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原则,将“人民主体性”转化为“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法定程序,并以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实现人民主权的实践转化;在经济领域创新“三次分配”机制,通过“共同富裕”目标实现主体性的物质确证;在文化领域激活传统民本思想的现代转化,将“民惟邦本”的古典智慧升华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形成主体性建构的历史连续性。其二,在价值论层面突破“工具性民本”的伦理局限,将“民本”的群体关怀与马克思主义的民主理论相结合,构建权利与义务统一的现代民主体系,通过法治保障选举权、参与权、监督权等公民权利,使民主从统治者的道德施惠转变为人民自我实现的制度路径。其三,在实践论层面超越传统“静态和谐”治理模式,以“共建共治共享”的动态治理哲学重构政治共同体,将“以人民为中心”嵌入政策制定与执行全过程,以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制度创新超越了西方个体本位的代议制民主范式,推动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从抽象理想向具象治理实践的跃迁,将民主从“权力制衡技术”升华为“人民主体价值”的实现方式。
(二)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以结果为导向的实质民主观
在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接续奋斗历程中,广大人民群众不仅是这项宏伟事业的建设主体,更是共享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成果的承载主体。习近平指出,“现代化的最终目标是实现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13)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的奋斗目标和规划部署蕴含着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是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生动呈现。列宁提出,“只是从社会主义实现时起,社会生活和个人生活的各个领域才会开始出现迅速的、真正的、确实是群众性的即有大多数居民参加然后有全体居民参加的前进运动”(14)。只有社会主义才能确保民主不仅仅是形式与程序上的民主,而是事实上和本质上的“以人民为中心”,而不是以资本或其他集团的利益为中心,保证现代化建设中“人民为中心”的正确方向,确保现代化成果为人民共享。美国学者科恩曾提出,民主的实质比它的形式要重要得多,“我们必须牢记民主的存在与否,不取决于任何形式的制度,而取决于实际决策过程的性质。”(15)
中国式现代化的民主观在实践层面展现出显著的实质正义特征,将本体论承诺转化为治理效能,实现价值导向、制度创新与治理效能的辩证统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是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导的经济制度,根本上改变了西方国家资本支配国家权力的政治运行逻辑,超越了西方国家资本对公民民主权利的主导与宰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为以人民为中心、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指向的实质民主的实现成为可能,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对人民权利的保障、对人民根本利益的维护、使亿万人民摆脱贫困奔向共同富裕的实践,从根本上来说得益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坚强保障和物质支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构建了“选举民主—协商民主”的复合民主结构,并通过“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和制度建立了高度负责型和回应型的各级人民政府,不断回应人民需要以及对美好生活的期待;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协商等协商民主制度、城乡居民自治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人民参与和管理现代化进程中的国家各级事务;通过人民民主将反映和表达人民群众根本利益、长远利益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战略目标与人民群众的当前利益、局部利益的有机地统一起来。如“精准扶贫”政策通过基层民主协商、村民大会、“四议两公开”等民主程序确定帮扶对象,充分调动群众参与的积极性,使群众在扶贫过程中真正成为主体,体现了人民当家作主的原则。再如“开门编规划”的民主参与形式,汇聚民众理性与智慧,促使民众思考国家长远利益,克服短视民粹现象,切实一步一个脚印、稳扎稳打地推动现代化建设。通过上述制度安排,中国式现代化民主观践行了实质民主的价值追求,实现从“形式正义”到“实质正义”的范式突破,既克服了西方民主不足的“资本至上陷阱”,(16)直接指向人民利益的实质目标,又克服了民主泛滥的“民粹主义陷阱”,既避免了西方民主的空转危机,又实现了决策科学性与民意代表性的统一。这种以人民为中心、以结果效能为导向的民主模式,不仅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路径参考,更在哲学层面证明了“民主真实性”的可能形态,成为人类政治文明演进的重要里程碑。在全球政治文明层面提供了以“人民性”为核心的治理方案,彰显了中华文明传统与现代性辩证统一的哲学智慧。
二、民主认识论:从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中获得对民主建设的规律性认识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对民主建设与发展规律的认识是基于唯物史观的认知基点,将民主视为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互动的产物,而不是抽象的理论框架,民主发展的规律与逻辑均来自实践并受实践检验,如“枫桥经验”从基层治理实践中提炼出“依靠群众就地化解矛盾”的民主治理逻辑。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实践不仅仅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范畴,也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和方法论依据,基于实践来认识现代化进程中的民主问题,才能获得关于民主的规律性和真理性认识,才能跳出西方学者写在学术著作或教材课本上的“刻板定理”,形成基于民族和国情、基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独特的民主观。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独特民主观,不是中国共产党或中国人民的主观臆想,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现代化的实践探索中形成的关于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规律性总结和正确观点,深深扎根于以唯物史观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突破西方民主理论的形而上学局限,打破“民主终结论”的历史唯心主义民主认识论。
(一)以文明主体性消解依附性发展的话语霸权,确立自主演进的民主成长路径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民主政治发展突破了西方中心主义的认知框架,确立自主演进和实践检验的民主认识论。现代化进程中健康的民主一般具有内生性的成长规律,体现为具有主体性与自主性的民主道路探索、逐渐完善的制度建构与发展过程、具有自身特色与现实性的民主制度。民主是一国民情、政治、历史、文化传统和阶级结构基础上的权力制约与权利保障的制度安排,那些已经被证明是比较成功的民主模式,都是适合自己国情、带着自身“文化基因”的民主制度,即主要从一国文化母体中“生长”出来的,都属于“内生型政治现代化模式”,“一个具有伟大的悠久历史传统的民族,它的优秀历史文明应适应时代的新需求而变化,绝不能遭到拋弃或鄙视。”(17)我们在现代化的实践中认识到,民主不能靠简单移植,要在自己的实践发展中探索适合自己的道路。经历现代化和民主建设的曲折之后,邓小平多次强调“中国要搞现代化,绝不能搞自由化,绝不能走西方资本主义道路”,“我们讲民主,不能搬用资产阶级的民主,不能搞三权鼎立那一套。”(18)习近平指出,“一切成功发展振兴的民族,都是找到了适合自己实际的道路的民族”,(19)那些成功实现现代化的国家,无论是内源型现代化还是外源型现代化国家,都进行了政治领域的重大变革,其政治改革和民主建设都进行了基于本国国情的道路选择和制度探索,都注重遵循民主成长的内生性因素。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坚持政治发展的主体性与自主性,成功探索出确立适应现代化建设的“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的“三位一体”的民主政治发展道路。
中国式现代化开创的民主发展道路,既非对西方民主理论的简单移植,亦非传统治理模式的机械延续,而是突破依附性理论的窠臼,通过激活文明基因中的主体性意识,将文明主体性转化为制度建构的基因密码,在现代化转型中实现了传统治理智慧的创造性激活与制度理性的自主性生长。中国通过文明基因的现代解码,打破了西方现代化理论所预设的“现在存在于西方发达国家的民主社会是世界其余各国的可靠样板”(20)的线性民主进化论。从文明主体性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民惟邦本”的治理理念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实现价值耦合,“和而不同”的传统哲学智慧转化为政治协商制度的程序设计,这种制度创新既非简单回归礼治传统,亦非机械移植代议制民主,而是将文明基因中的集体理性如“天下为公”的价值共识转化为现代国家治理的底层逻辑。如“十四五”规划编制过程中,通过“群众建言—专家论证—民主协商”的复合机制,使超过百万条公民意见转化为国家战略的有机组成,这种政策形成机制既超越了西方利益集团游说的碎片化决策模式,也突破了传统依附理论设定的发展路径依赖。从方法论层面看,中国创造了制度演进的双向运动机制,构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选举+协商”的复合型民主生态系统,将文明主体性转化为破解依附困境的实践工具,创新民主集中制和中国共产党群众路线的实践方法,实现现代化与政治稳定的协调推进,破解了亨廷顿提出“现代性带来稳定,现代化引起动乱”(21)的“亨廷顿悖论”,即后发国家制度化困境。从民主进程看,从国内外经验教训中认识到民主进程的渐进性,不搞政治制度上的“休克疗法”与“飞来峰”。现代化作为一个整体的历史进程,既要重视生产力的发展,同时,又要重视上层建筑的反作用,并根据经济基础变革和生产力发展状况不断进行改革调整,推动民主建设与经济基础变革和生产力现代化的协调一致。民主发展既有长远的发展战略,又有阶段性目标,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民主的发展超过了限度,则会走向反面。没有民主的现代化是不完整的现代化,也是容易走入“陷阱”的现代化;没有现代化的民主,也将落入贫困和混乱。现代化的历史表明,现代化进程中既无法在不变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基础上片面推动生产力的大发展,也无法单方面搞上层建筑的“大跃进”,“不能想象突然就搬来一座政治制度上的‘飞来峰’”,(22)不能把民主作为一个抽象的前提加以设定,在没有打好“地基”之前就直接建设民主政治的“高楼大厦”,搞民主政治建设的单向突围,而是要根据生产力和经济基础状况进行变革和调整,逐步完善民主制度。中国式现代化的巨大成就说明了民主政治建设与经济基础和生产力现代化协同推进、并行发展的重要性与优越性。
(二)以“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民主三维评价标准,突破西方单一的“竞争性选举”认知框架
中国式现代化的民主观重构了民主政治的评价坐标系,突破将民主异化为程序技术的思维定式,转向对民主实践主体、过程与效能的整体性把握。当西方将选举竞争简化为民主的黄金标准时,中国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人民立场与中国“民心政治”的传统理念发展为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价值内核,并以此作为民主评价的标准。二战后的西方学术界制造了民主“科学化”“指数化”“民主=选举”的学术话语传统,垄断了民主评价标准,有没有竞争性的选举成为他们评判一个政体是否民主的最重要甚至唯一标尺,至于人民是否真正能当家作主则显得不重要了。对此,西方学者也曾批评到把精英之间的选票竞争定义为民主,是以现实主义的名义“剥夺了民主的所有伦理内容”。(23)中国式现代化的民主观坚持民主评价的唯物史观标准,从事实出发而不是从定义与理论出发评价民主与否。习近平指出,我们的民主是“是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民主”,(24)以客观实践和效果为基础的民主评价观,摒弃民主认知上的形而上学。
习近平指出:“一个国家民主不民主,关键在于是不是真正做到了人民当家作主,要看人民有没有投票权,更要看人民有没有广泛参与权;要看人民在选举过程中得到了什么口头许诺,更要看选举后这些承诺实现了多少;要看制度和法律规定了什么样的政治程序和政治规则,更要看这些制度和法律是不是真正得到了执行;要看权力运行规则和程序是否民主,更要看权力是否真正受到人民监督和制约。”(25)这一标准把政治制度民主与否的判定标准真正落实到人民权利的实现和保障上,落实到现代化进程中国国家治理结构和治理效果上,落实到“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效能上,突破西方政治学关于民主评价中从概念定义和数据模型出发的理论与现实颠倒的形而上学思维,从实事求是这一唯物史观的基本要求出发,对政治制度民主与否进行的科学评价,衡量一个政治制度是否民主的标准就不再是存不存在自由的、竞争性的多党选举。一项基于23个国家民众对民主的认知调查显示,最认同“民众能够畅通表达利益诉求”(91.4%)、“民主应注重解决人民实际问题”(91.4%)、“国家权力应得到民众有效监督”(91.2%)等。其中,发展中国家对于“民主应注重解决人民实际问题”(92.4%)认同度最高,全球18-35岁青年对于“民众能够畅通表达利益诉求”原则的认同度最高,达到92.3%。(26)民主的真谛不在于形式上的对抗性表演,而在于能否形成最广泛的政治共识、构建最真实的参与渠道、实现最有效的治理变革。实际上,民主的传统有两种,一种是源自古希腊,发展繁荣于英美的西式民主传统,这是众人所熟知的民主。第二种是源于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中的民主传统,这一民主传统与近代以来社会主义运动紧密结合、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追求民主建国的革命历程结合、与中国传统民本思想在当代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结合,力图回归到人民民主的本质。(27)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民主就是对第二种民主传统的承接与发展。这一民主传统在西式民主话语和民主理论霸权之下被国内外学术界忽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一直不能得到充分有效、科学理性的国内外学术表达。我们要打破西式民主标准的框定和思维盲区,就必须回到第二种民主传统中,构建中国自主的民主政治学术知识和学术话语体系。我们党提出“八个能否”“四个要看、四个更要看”“六个切实防止”,是对西式民主传统和民主标准的超越,是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典范:评价一国民主与否,从一个国家的制度运行的事实与效果出发,从人们的实际感受出发,从民主效能是否服务于现代化建设的要求来评价,以是否能让人民过上好日子为旨归来评价,回归民主的本质功能,满足人民过上好日子的真正需求。从功能视角来评价民主,而不是从形式视角来评价民主。正如有学者指出,形式上看似‘民主’的体制(如有定期选举和多党竞争)运作起来也未必符合民主的原则,今天的西方民主已经是“异化后的民主、去势后的民主、无害化的民主、去功能化的民主。”(28)
当西方政治理论陷入“选举原教旨主义”的认知困境时,中国民主实践的三维标准为重构民主认识论提供了新的可能。这种认识论突破不仅在于拓展了民主的主体边界,更在于将民主理解为持续的认识深化过程,并最终以实践效能作为检验标准。
三、民主方法论:以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的系统方法创新民主实践
民主的方法论解决民主如何实现和运行的问题,主要涉及民主的制度机制。现代化是一个全面的系统工程,“必须坚持系统观念。万事万物是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只有用普遍联系的、全面系统的、发展变化的观点观察事物,才能把握事物发展规律,”(29)以系统的、整体的观点去看待和认识事物,其最基本、最核心的要求就是把握整体性。“现代化的过程不局限于社会现实的一个领域,而是包括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30)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的现代化。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探索中,我们认为民主不仅是政治领域的制度安排,不仅涉及谁的民主、由谁来真正统治国家,还涉及以什么样的制度形式、在何种领域与在哪些范围来进行统治,即现代化进程中的民主建设要适应现代化的全面性的要求,树立系统观念,坚持民主发展的系统性、整体性与全面性。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建构制度聚合、过程嵌入、效能导向的民主实践体系,在方法论上解决了民主的规范与民主的现实之间的结构性困境,实现“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开创超大规模国家的民主实践路径,避免西方民主中程序正义与实质正义的割裂、现代化与民主化的紧张与冲突。
(一)坚持系统观念,发展全链条全过程的民主程序与制度体系
马克思主义认为,“世界不是既成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31)“在民主制中,任何一个环节都不具有与它本身的意义不同的意义。每一个环节实际上都只是整体人民的环节”,(32)让每一个民主环节真正成为“整体人民”能够参与和掌握的具体过程,“形成完整的制度程序和参与实践,保证人民在日常政治生活中有广泛持续深入参与的权利”。(33)运用这一思维方式,我们可以看到民主不是一个既成的安排,而是一个过程性的、不断完善的制度体系安排,真正的民主创新必须植根于对社会矛盾运动系统的、历史的、辩证的把握。
中国式现代化的民主观遵循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的世界观与方法论,确立系统观念和整体性思维,明确了民主是一套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体系;明确民主不仅有选举一种方式,还有政治协商的方式;民主不仅有选举民意代表,还有参与决策、管理、监督和立法、行政、司法等方面;明确了民主不仅在政治领域发展,还包括经济与社会文化领域的民主要求。认为民主的程序不是一次性的选举过程,认为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等都是民主过程的重要环节,实现民主程序的全链条无隙缝衔接,互相贯通。中国民主的实践创新体现在制度构建的全链条贯通,将民主从“竞争性选举”的单一维度扩展为“人民当家作主”的系统工程。在民主具体环节上,创设“选举、协商、决策、管理、监督”五大环节的闭环设计,使民主从“瞬时性权力让渡”升级为“持续性权力行使”的完整制度链。全链条对应社会再生产过程的不可割裂性,全方位反映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交互作用,全覆盖体现群众史观对民主主体的终极关怀。在纵向维度上,形成了“顶层设计—基层探索”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双向互动的制度创新通道;横向维度上,政党协商、人大协商、政府协商、政协协商、人民团体协商、基层协商以及社会组织协商等七大协商渠道协同运作。资本主义民主制度将公民参与简化为选举,民主即是让人民在几个相互竞争的精英团体中进行选择,民众参与政治的作用便被限制在四、五年选一次政府的范围内,造成民主的窄化、异化,民主政治异化为选举政治。当前西方民主仅聚焦选举环节,造成“政治领域的工段化”,割裂“意愿形成—决策制定—执行监督”的有机联系,“在实践中,民主的‘全过程’被放弃,民主政治原则被国家机器暴力地分割裁剪成为最高权力的分权制衡、一人一票的竞争选举与轮流执政的党派政治等相互分离的单元,且在每个单元中民主原则仅仅是碎片化地被使用,以期呈现出最低程度的形式民主。”(34)当前,当西方政治学者还在追问“审议型小型公众”(Deliberative Mini-publics)(35)是否提升民主质量时,中国早已经在基层民主、政党协商、政府协商等各层级实践中充分实现了这一寻求共识的民主精神。
(二)坚持整体思维,发展全方位全覆盖的形式与内容相统一的民主
马克思曾批判资产阶级民主的“政治领域隔离”,认为资产阶级政治革命虽然实现了“政治国家”与宗教的分离,却在社会层面制造了新的分裂——将人割裂为“抽象的公民”与“现实的私人”,导致政治领域与社会经济生活的根本性隔离。这一批判不仅瓦解了资产阶级政治哲学的合法性,也为理解当代民主危机提供了钥匙,即真正的民主必须打破政治与经济的二元隔离,在社会解放中实现人的全面自由。现代西方代议制民主仍遵循“政治隔离”的逻辑:公民在投票时“平等”,但在政策制定中被资本利益集团操控如美国的游说政治,同时,种族、性别等身份政治议题的兴起,掩盖了阶级矛盾这一根本问题,“黑命贵”运动未触及资本主义种族化剥削结构。毛泽东曾提出:“民主必须是各方面的,是政治上的,军事上的,经济上的,文化上的,党务上的以及国际关系上的,一切这些,都需要民主。”(36)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视域下的全方位民主必须穿透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领域,在整个社会生活的领域中贯彻民主的原则与逻辑,推动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中国式现代化的民主观坚持整体思维,强调现代化进程与民主发展的整体协调与发展一致性,民主政治是现代化建设的要求,亦是现代化进程中的伴生物。在整体思维指导下,不片面强调民主的制度形式,不为了民主而民主,不超越发展阶段片面追求民主建设的突飞猛进,而是赋予民主制度以坚实的内容支撑,把人当作现代化的最终目的,认为民主不仅仅是一项政治领域的权利要求,更是经济上物质富裕的基本诉求以及社会与文化领域平等权利和精神享受的满足,现代化进程中的民主是要满足人们内在的自我提升与自我发展的需要。全方位、全覆盖的民主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深刻关联,与现代化的整体性和总体性要求深度契合,贯穿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各个领域,覆盖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各个环节。民主建设不仅在经济领域满足人民富裕起来的需求和愿望,更要满足人们对生存和发展权利、社会公平正义、丰富的精神文化和社会生活以及美丽清洁的生态环境的要求,发展全方位全覆盖的民主。在民主形式和途径上,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发展多种民主形式和途径,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的并存,既有选举民主,也有不同层次的政党协商、人大协商、政府协商、政协协商、人民团体协商、基层协商以及社会组织协商;既有现实空间参与渠道和途径,也有虚拟空间的网络群众路线和网络政治参与,是一种全时空、全方位的民主,在纵向时间和多维空间中享有完整行使民主的权利,充分参与现代化建设进程。通过建构全方位、全覆盖的表达与参与渠道和公正分配公共利益的制度框架与运作机制来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真正实现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化。西方现代化进程中的自由民主理论均强调政治民主与政治平等,而忽视经济民主与经济平等,在后续的民主理论创新中,无论是参与式民主理论还是协商民主理论,实际上均把民主的重点放在政治领域,始终无法采用整体思维和系统观念去看待民主发展的整体性、全面性以及与经济基础的深刻关联性。列宁曾深刻批判:“资本主义社会里的民主是一种残缺不全的、贫乏的和虚伪的民主,是只供富人、只供少数人享受的民主。”(37)今天,这种情况未变得更好而是更坏,一些国家已变成“1%的人拥有、1%的人治理、1%的人享受”的社会,民主已经从现代化进程中的经济权利保障、阶级矛盾调解功能变成为大资本及其代理人投票的游戏。
结语
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独特民主观,以“人民主体性”超越“资本中心性”,突破“民主原教旨主义”的认识论陷阱,发展出“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的系统实践范式,使民主从政治领域的程序性安排升维为文明形态的整体性再造。中国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方法推动的民主实践创新,正为人类探索“优质民主”提供着超越对抗思维、平衡秩序与活力的新方案,为人类现代化进程中的政治文明发展提供了新选项。这种探索的价值不在于输出替代模式,而在于证明了一个更具文明包容性的真理:民主的生命力不在于模仿某种固定模式,而在于能否在本国土壤中生长出保障人民主体地位和根本利益的制度形态。真正的民主进步,必然是各国人民在历史辩证法指引下自主书写的多元叙事。
注释:
①本书课题组:《党的二十大精神专题十二讲》,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35页。
②《列宁专题文集论社会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98页。
③张明澍:《中国人想要什么样民主:中国“政治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85页。
④王升平:《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认识论基底:一种政治哲学视角的考察》,《科学社会主义》2024年第6期;彭姝:《全过程人民民主理论的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探析》,《山东社会科学》2024年第6期。
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15页。
⑥(24)(29)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37、37、20页。
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20页。
⑧⑨⑩(3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9、40、41、39页。
(11)《习近平著作选读》第2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530页。
(12)(22)(25)(33)习近平:《论坚持人民当家作主》,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年版,第318、80、335-336、177页。
(13)《习近平重要讲话单行本(2023年合订本)》,人民出版社2024年版,第7页。
(14)《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01页。
(15)[美]科恩著,聂崇信、朱秀贤译:《论民主》,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41页。
(16)吴忠民:《中国现代化新论》,商务印书馆2023年版,第140页。
(17)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中国的现代化之路》,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271页。
(18)《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23页、第195页。
(19)习近平:《在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5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5页。
(20)(21)[美]塞缪尔·P.亨廷顿著,王冠华,刘为等译:《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8年版,第Ⅲ、37页。
(23)Mackie, Gerry. "Schumpeter's leadership democracy". Political Theory. Vol. 37, No1. 2009. pp. 128-153.
(26)段丹洁:《中国民主实践与现代化发展全球调查报告2023》发布,https://www.cssn.cn/skgz/bwyc/202403/t20240328_5742661.shtml2024-03-28.
(27)李菱主编:《如何看待当代中国社会思潮及影响》,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30-31页。
(28)王绍光:《民主四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2年版,第61页。
(30)[美]塞缪尔·亨廷顿等著,罗荣渠主编:《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版,第28页。
(3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98页。
(34)王炳权:《西式民主在民主原则、精神、能力上的弱化劣化》,《北京日报》2023年3月13日。
(35)Robert E. Goodin, et al. Goodin, and E. R.. "Deliberative Impacts: The Macro-Political Uptake of Mini-Publics." Politics & Society. vol. 34, No. 2, 2006. pp. 219-244; Beauvais E, Warren M E. "What can deliberative minipublics contribute to democratic systems?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 Vol. 58, 2019. pp. 893-914;
(36)《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69页。
(37)《列宁专题文集论马克思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6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