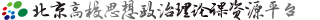【摘要】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水平,提升亲和力和针对性,需要践行五个“有”:一是言之有物,即要以问题为导向,注重对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的分析和阐释;二是言之有理,即要注重对思想的内在逻辑的梳理和阐释,把道理讲深、讲透,以理服人;三是言之有据,即要注重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论述,以充分而可靠的理论依据和事实依据作为依托和支撑;四是言之有“马”,即要注重马克思在其成熟时期的理论研究和论述,杜绝没有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课;五是言之有“我”,即要以教师本人的学术研究作为依托和支撑,在教学中展示和体现自己的研究成果、研究特色。
【关键词】思想政治理论课;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问题导向;以理服人
【作者简介】牛变秀,北京农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王峰明,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原文出处】《思想理论教育导刊》(京),2022.10.83~91
办好思政课是习近平总书记非常关心的一件事。他强调:“思想政治理论课要坚持在改进中加强,提升思想政治教育亲和力和针对性,满足学生成长发展需求和期待”,“要坚持不懈传播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抓好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为学生一生成长奠定科学的思想基础”。[1](P377-378)可以说,只有切实改进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方法,提升亲和力和针对性,才能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课教学水平和效果,落实思政课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笔者基于多年的教学实践和体验,提出马克思主义理论课教学需要重视五个“有”——言之有“物”、言之有“理”、言之有“据”、言之有“马”、言之有“我”。
一、言之有“物”
所谓“言之有物”,指的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课必须具有鲜明的问题意识和问题导向,要充分了解问题,敢于直面问题,善于疏导和分析问题。既不能忽视问题,更不能无视和回避问题。马克思指出:“问题就是公开的、无畏的、左右一切个人的时代声音。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2](P289-290)在此意义上,回避问题就意味着置时代发展潮流于不顾,这样的理论课是没有出路的。就马克思主义理论而言,一方面,它来自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实践需要,蕴含着对各种重大现实问题的不懈探索和科学分析;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自诞生之日起就受到各种非马克思主义者或反马克思主义者的攻讦和批评。它是在同各种错误思潮的斗争中不断成长、成熟起来的,蕴含着对各种重大理论问题的辨析和阐释。在此意义上,能否讲好马克思主义理论课,关键就在于能否把这些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讲深、讲透,让学生通过问题切实领会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
随着改革开放事业的推进,不仅出现了各种棘手的现实问题,也把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摆到马克思主义理论课上来。例如,如何看待资本与剥削的关系问题?有人认为,剥削意味着一个人的贡献与其收入不成比例,即收入大于他所做的贡献;以此作为衡量标准,就会看到不仅工人受资本家的剥削,资本家也会受工人—劳动者的剥削。这种观点否定了资本和剥削之间的必然联系,由此引发的问题是:如果说资本并不—定具有剥削性,那么,如何看待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和资本剥削理论?反之,如果说剥削是资本的本质特征,只要是资本就一定会剥削劳动者,那么,如何看待社会主义条件下的资本剥削问题?如何看待资本剥削与社会主义的关系问题?又如何看待资本和资本家在生产中的作用问题?资本的历史合理性究竟何在呢?还有,如何看待资本与生产要素的关系?如果说资本是生产要素,那么,资本的剥削性又是从何而来的呢?如此等等。可以说,这些问题是多年来马克思主义理论课教学所面临的最具挑战性的问题,也是不应回避且回避不了的问题。
其实,对经济社会发展中出现的种种现实问题,我们党和国家不仅予以高度重视,而且一直在努力寻求解决问题的有效路径,也出台了各种政策措施。例如,早在2003年召开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就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和五个“统筹”,即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这无疑是为处理和解决改革开放新时期经济和社会发展重大问题而做出的顶层设计和布局。同时,党和国家也逐步注意到了一些重大现实问题与资本的内在联系,并把规范和引导资本行为的任务提到议事日程上来。2021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正确认识和把握资本的特性和行为规律”,要“有效控制其消极作用”,“要为资本设置‘红绿灯’,依法加强对资本的有效监管,防止资本野蛮生长”。[3]
资本的特性和行为规律究竟是什么?如何正确认识和把握资本的特性和行为规律?这是重大理论问题,也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课教学中绕不开的问题。2019年3月18日,习近平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指出:“思政课教师掌握着课堂的主导权和话语权,一定要自觉弘扬主旋律,积极传递正能量。遵守纪律,不意味着不能讲矛盾、碰问题。有的教师怵于思政课的意识形态属性,担心祸从口出,总是绕开问题讲、避开难点讲。只要坚持正确政治方向,立足于引导学生坚定理想信念,全面客观看问题,就不用担心在政治上出问题。”[4]因此,面对上述问题,一方面,需要认真研习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相关论述;另一方面,要对种种错误观点予以有力驳斥和回击,决不能在大是大非面前失语,更不能失位。敢于直面问题,才能有的放矢和言之有物,才具有亲和力和针对性。一团和气的课堂决不是好课堂,无学术交锋或不敢进行学术交锋的教学必须加以改变。否则,就会严重制约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的教学水平和效果。
二、言之有“理”
所谓“言之有理”,指的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课必须把道理讲清楚,要以理服人,不能装腔作势、不讲道理,更不能强词夺理、以势压人。理论是“理”之论,是道理的铺陈和展开,而理论之“理”则贯通和体现在概念、逻辑、论证等各个方面。只有做到概念明晰、逻辑严密、论据翔实、论证充分,才能把道理讲清楚,才能做到言之有理。
例如,作为马克思的两大理论发现之一的剩余价值学说,实际上就是资本剥削理论,这一理论又建立在科学的劳动价值理论的基础之上,决不能把它们割裂开来。因为,剩余价值的本质和来源问题与价值的本质和来源问题是一致的,剩余价值不过是商品价值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所采取的一种特殊形式。在此意义上可以说,剩余价值理论和资本剥削理论是一种广义的劳动价值理论。而对于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在一些人看来,由于“很难从中发现任何论证的痕迹”,所以,“可以把它从一种形而上学的说法变成为一种假说”。[5](P42)如果说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仅仅是一种假说或假设,就很难说有什么道理可言,更遑论以理服人了。然而,这是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极大误解。马克思曾明确表示:“即使我的书中根本没有论‘价值’的一章,我对现实关系所作的分析仍然会包含有对实在的价值关系的论证和说明。”[6](P281)这种论证和说明可以概括为:第一,两种不同商品相交换,就每一次的情况来看,其交换比例显然是随机的和不确定的;但从长期趋势来看则会形成一种确定的比例和量的关系。第二,这种“量”的关系显然是比较、计算和折算的结果。而两种商品要进行量的比较、计算和折算,就必须具有或包含了相同的“质”。第三,这种相同的质自然不是商品的使用价值,从而也不是创造使用价值的具体劳动,而是凝结在商品中的一般人类劳动。可见,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对商品价值的本质和源泉的论证是极为严密的,怎么能说是一种缺乏论证的假说呢?
国内国际学界对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提出了诸多质疑和批评,尽管这给课堂教学带来巨大挑战,但是,无论是反对还是赞成这一理论,都必须把握其中的逻辑和道理。就反对者而言,如果不能推翻其内在逻辑和道理,那么,这种反对就是无效的;就赞成者而言,如果不能说明其中的内在逻辑和道理,同样也是无效的。就资本剥削问题而言,只要把握了劳动价值论的内在逻辑和道理,资本和剥削的关系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剥削始终是资本家对雇佣工人剩余劳动的无偿占有,既不存在雇佣工人之间的剥削,因为他们都是创造价值和剩余价值的劳动者;也不存在资本家之间的剥削,因为他们都是对他人剩余劳动和剩余价值的无偿占有者;更不存在雇佣工人对资本家的剥削。因为在现实中,利润总是来自工人的剩余劳动,所以,即使把资本家的一部分利润交给雇佣工人,也不过是工人把自己的剩余劳动收回而已,何来工人对资本家的剥削呢?
当然,有比较才有鉴别。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内在逻辑和道理讲清楚,就要在不同理论之间进行比较,不能唱独角戏。通过比较就会发现,效用(边际效用)价值论混淆了商品的价值和使用价值,而供求价值论(均衡价值论)则混淆了商品的价值和价格,它们在逻辑上就难以自洽,更遑论科学性了。只有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才把商品使用价值、交换价值、价值和价格科学地区别开来,不仅在逻辑上是自洽的,对现实问题的解释力也毋庸置疑。此外,还要重视辩论的作用。辩论是把握逻辑、参透道理的重要方法。通过辩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内在逻辑和道理才能入心入脑,真正触动并进入学生的思想世界。
三、言之有“据”
所谓“言之有据”,指的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课必须以经典著作作为立论的理论根据,以现实社会存在和历史发展作为立论的事实根据,不能靠拍脑门讲课,不能主观武断,更不能信口雌黄。
例如,在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新时期,有人提出了“资本二重性”理论。他们或者认为,除了“剥削”的特性,即无偿占有工人剩余劳动创造的剩余价值,资本还具有保值和增殖的特性,因为凡是资本都要追求价值的保值和增殖。如果说,剥削特性是资本主义社会的资本所特有的,体现了资本主义社会资本的个性,那么,增殖特性则是一切资本所共同具有的,体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资本和社会主义社会的资本的共性。换言之,在保值和增殖这一点上,社会主义社会的资本和资本主义社会的资本并无二致。或者认为,由于资本一方面以机器、厂房和原材料等物质形式存在,所以具有物质属性;另一方面,由于资本是存在于资本家阶级和雇佣工人阶级之间的剥削与被剥削的社会关系,所以具有社会属性。前者是一种技术—物质关系,后者则是一种经济—社会关系;前者体现了资本的一般性并为一切历史形式的社会制度所共有,后者则体现了资本的特殊性并为资本主义制度所特有。以“资本二重性”理论为基础,一些人不仅区分了“资本主义资本”和“社会主义资本”,而且进一步把社会主义资本叫做“公有资本”或“国有资本”。
可以说,“社会主义资本”概念和“资本二重性”理论,就是拍脑门的结果,既缺乏理论依据,也有悖于社会存在和历史发展的实际情况。因为,我们通过文献检索发现,马克思的著作中从来没有出现“公有资本”或“国有资本”这样的概念,也找不到“社会主义资本”或“共产主义资本”这样的提法。马克思一再强调:“资本的增殖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唯一目的”。[7](P270)其中,“资本的增殖”的德语原文是“die Verwertung des Kapitals”,[8](P251-252)其英译文则是“self-expansion of capital”。[9](P241)可见,“增殖”意指资本的“自我扩大”。那么,究竟如何理解资本的这种自我扩大呢?能否把这种自我扩大和资本的剥削特性分割开来呢?当然不能。因为,马克思明确地把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看作资本主义生产过程(而非资本本身)所具有的二重性。[10](P207)其中,“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的德语原文是“Arbeitsprozeβ und Verwertungsprozeβ”,[11](P192)其英译文则是“The labour-process and the process of producing surplus-value”。[12](P173)可见,资本的自我扩大即增殖所指的,实际上就是剩余价值的生产和创造,就是资本家对工人剩余价值的无偿占有。对此,马克思讲得非常明确:“剩余价值的创造”就是资本“价值的自行增殖”,因此,“在生产过程内部,价值增殖和剩余劳动的生产(剩余时间的对象化)完全是一回事”。[13](P384)这一道理,也体现在马克思的如下论述中:“价值只是对象化劳动,而剩余价值(资本的价值增殖)只是超过再生产劳动能力所必需的那部分对象化劳动而形成的余额。”[13](P377)因此,决不能把价值增殖的特性和剥削的特性一分为二,看成是资本的两重特性,它们是资本的同一种(也是唯一)特性的不同表达方式。只要是资本,就具有剥削的特性;只要是剥削,就是对劳动者剩余劳动的无偿占有。资本剥削不过是无偿占有劳动者剩余劳动的一种特殊历史形式。
当然,一些人会问,无论在资本主义社会还是在社会主义社会,无论在私营企业还是在国有企业,劳动者都要付出剩余劳动,何以在前者这种剩余劳动体现着资本家的剥削,而在后者就不是剥削了呢?对此,我们仍然可以在马克思的著作中找到具体论述。在谈到原始共同体的生产时,马克思指出:“个人在维持其生存所必需的直接劳动”即必要劳动之外,总是要以这样那样的形式完成一定的剩余劳动。但是,由于“这种劳动无论对于共同体或作为共同体成员的每个个人来说都是必要的”,所以,“这种劳动就不是个人完成的剩余劳动,而是他的必要劳动的一部分,这种劳动所以必要,是为了使他把他自己作为共同体成员再生产出来,从而也把共同体再生产出来,而共同体本身则是个人从事生产活动的一般条件”。[13](P523)这就表明,在公有制(如原始公有制)条件下,劳动者的必要劳动与剩余劳动不具有对抗性,必要劳动是劳动者为满足自己作为“个人”的需要(如食物)所付出的劳动,而剩余劳动则是劳动者为满足自己作为“共同体成员”的需要(如道路等公共建筑)所付出的劳动。剩余劳动来自于劳动者,最后又回归于劳动者,可谓“羊毛出在羊身上,羊毛又用在羊身上”。在这里,并不存在劳动者的剩余劳动被非劳动者无偿占有的情况,因而也就不存在剥削关系。与此不同,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剩余劳动时间只是作为对立物,只是同必要劳动时间对立地存在着,因此,资本把必要劳动时间作为它的再生产和价值增殖的必要条件”。[13](P542-543)就是说,这种剩余劳动只是对资本的再生产即对资本的价值增殖来说,才是必要的;对工人而言,它不仅不是必要的,反而是有害的。换言之,劳动者的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是一种对立的关系,剩余劳动被资本家无偿地据为己有,进而形成对劳动者单向度的、不平等的经济剥削关系。
总之,从马克思《资本论》文本来看,“资本二重性”理论的错误,或者在于:把增殖特性和剥削特性看作两种不同的特性,而实际上它们是同一种特性的不同表达形式,指的都是资本家阶级对工人阶级所创造的剩余价值的无偿占有;或者在于:把资本等同于物,看不到资本在本质上是一种生产关系,是通过物所实现的对工人的统治和剥削关系。“资本二重性”理论缺乏起码的理论根据,不仅扰乱了人们的思想,使人们无法把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本质地区别开来;而且严重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和立场,偏离了社会主义的基本方向和目标。
四、言之有“马”
所谓“言之有马”,指的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课必须充分重视和尊重马克思本人的论述,避免出现马克思“缺席”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课,更要杜绝非马克思或反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课。因为从根本上讲,马克思主义来源于马克思毕生的理论探索和创新,马克思主义的多样化发展不会也不能脱离其源头的基本原则和立场。值得注意的是,一些人不认为马克思思想从一开始就是错误的,但认为随着时代变迁,马克思思想不够用了,需要扩展和补充;甚至认为已经过时了,需要修正和重建。他们打着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旗号,却在背离马克思思想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例如,在资本是否是生产要素的问题上,第一,就其内涵而言,马克思指出:“就劳动过程只是人和自然之间的单纯过程来说,劳动过程的简单要素是这个过程的一切社会发展形式所共有的。”[7](P1000)或者说,“它不以人类生活的任何形式为转移”,“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一般条件,是人类生活的永恒的自然条件”。[10](P215)就是说,劳动是由人引起、调整和控制的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过程,生产要素则是这一过程赖以进行的必要条件,无论在什么样的经济社会形态中,这些要素都是物质生产所不可或缺的。马克思区分了生产过程中的两种关系:一种是“技术关系”,一种是“权力—支配关系”,这是两种性质不同的关系,不能混为一谈。生产要素所体现的,是技术关系而非权力—支配关系。生产要素之所以是生产过程的必要因素,就在于它们在技术意义上是不可或缺的。
第二,就其外延而言,马克思指出:“劳动过程的简单要素是:有目的的活动或劳动本身,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10](P208)就是说,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是一切历史形式的物质生产的三个必要因素。由于“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二者表现为生产资料,劳动本身则表现为生产劳动”,所以,马克思说:“劳动过程所需要的一切因素:物的因素和人的因素,即生产资料和劳动力”。[10](P215)就是说,生产要素可以进一步区分为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生产资料是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的统一,构成生产过程的“物”(即死的)的要素,劳动者则构成生产过程的“人”(即活的)的要素。这就是众所周知的“三要素论”和“两要素论”。马克思在谈到资本剥削时指出:“形成流通行为的先导行为,即劳动力的买和卖,本身又是建立在先于社会产品的分配并作为其前提的生产要素的分配的基础上的,也就是建立在作为工人的商品的劳动力和作为非工人的财产的生产资料互相分离的基础上的。”[14](P427-428)就是说,劳动力的买和卖,是资本剥削的前提条件;而生产要素的分配即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的互相分离则是劳动力买卖的前提。可见,生产要素包括劳动力和生产资料两个方面。
第三,资本离不开一定的物,但物本身并不是资本;既不能把资本等同于物,也不能把资本看成生产要素。对此,马克思指出:“单纯从资本的物质方面来理解资本,把资本看成生产工具,完全抛开使生产工具变为资本的经济形式,这就使经济家们陷入种种困难之中。”[13](P594)例如,“罗西把资本同技术意义上的生产工具完全混为一谈了,这样说来,每个野蛮人都是资本家了”。[13](P594)很明显,生产工具或劳动资料是技术关系中的物所获得的属性,体现和反映的是生产过程中的技术关系和技术性质。技术性质无非是各种生产要素所具有的机械的、物理的、化学的和生物的性质,而由技术性质所决定的生产要素之间的关系便是技术关系。马克思提示我们要注意生产工具的技术意义和生产过程的“技术性质”。[10](P288)如果把资本看成物,看成物所具有的技术性质,“这一点就被利用来为资本辩护,把资本与一般简单劳动过程的一种要素混淆或等同起来,从而说什么用于生产另外一种产品的产品就是资本,原材料是资本,或者劳动工具,生产工具是资本,因此,资本是同一切分配关系和社会生产形式无关的、一般劳动过程的因素、生产的因素”。[15](P71)可见,生产要素是生产过程中的技术关系赋予物的规定,而资本则是权力—支配关系赋予物的规定。这是两种性质不同的规定,不能混为一谈。马克思指出:“从资本的观点看来,工资是单纯的生产关系,从工人的观点看来,却是分配关系。”[16](P160)就是说,一定量的货币额,对于资本家是可变资本,对于工人则是工资;前者是生产关系,后者则是分配关系或收入关系。可见,同一个物,在不同关系中会获得不同规定,决不能混为一谈。
显然,把资本看成生产要素,完全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和立场。究其本质而言,马克思主义理论之“流”(即多样性发展),是基于社会主义国家所处的历史条件和具体国情,以马克思思想为方法论指导,对各国社会主义具体实现形式即具体道路的探索。借口发展马克思主义而偏离和背离马克思思想之“源”,否定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和立场,就不成其为“流”。当然,马克思的思想也有一个从不成熟走向成熟的过程,要把马克思早期不成熟的思想与后期的成熟思想区别开来,不能搞“同质性”解读和引用。按照米克的说法,《哲学的贫困》“意味着马克思第一次试图直接从唯物史观来分析交换价值的经济范畴”,从而“恢复了当初劳动价值学说与唯物史观间的密切结合”。[17](P154)(需要指出的是,在米克看来,劳动价值论和唯物史观的最初结合是由亚当·斯密完成的,尽管这种唯物史观是“不成熟的”。这一论断值得商榷。)这表明,没有唯物史观的创立,就不可能有科学的劳动价值理论,也就不可能有科学的资本理论和剩余价值理论。
五、言之有“我”
所谓“言之有我”,指的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课必须以教师本人的学术研究作为依托和支撑,在教学中体现自己的研究成果、研究特色。在落实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的过程中,既要注重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连续性,也要注重各个阶段的不同要求。以研究为基础,通过理论研究带动和推动教学,恰恰是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的独特要求和鲜明特征。没有研究或不注重研究,就难以真正进入马克思的思想世界,难以理解和把握马克思思想的内在逻辑。只有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说服自己,让自己相信,才能去说服别人。如果连自己都不信,就更难让学生相信了。而要说服自己,使自己相信,就必须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
就现实问题而言,马克思主义理论提供的是分析问题的基本原则和方法论指导,而不是一劳永逸的现成答案。马克思一再告诫我们:“应当时刻记住,一旦在我们面前出现某种具体的经济现象,决不能简单地和直接地用一般的经济规律来说明这种现象。”[18](P405)就是说,决不能用理论直接去“套”现实,决不能用一般本质和规律直接去解释和说明现象。由于各种中介环节和中介过程的加入,事物的现象形态往往会偏离一般本质和规律,从而呈现出与一般本质和规律不同的甚至是截然相反的外部特征。只有把握这些中介环节和中介过程,才能打通事物的本质和现象之间的联系,获得对现象的本质性认识。事物的中介环节和中介过程是多样的,而非单一的;是具体的历史的,而非一成不变的。把握中介环节和中介过程,就需要从具体情况出发进行具体研究。
就理论问题而言,马克思对各种问题的分析和阐释,并非简单明白地摆在那里,需要深入文本进行发掘、整理和诠释,需要根据不断变化的现实情况进行新的理解和阐释,需要根据思想斗争的需要进行细致辨析。一方面,只有经过反复研究,才能准确理解马克思的一些重要论述。例如,在谈到计件工资时,马克思指出:“计件工资使资本家能与工头……签订按件计酬的合同,工头按照合同规定的价格自己负责招募帮手和支付给他们工资。”[19](P570)由于这些工头本身是劳动者,他们“在手工工场是组长,在矿井是采煤工人等等,在工厂是真正的机器工人”,[19](P570)所以,“在这里,资本对工人的剥削是通过工人对工人的剥削来实现的”。[19](P571)一些人往往以此为据,认为“工头”具有剥削者和劳动者的双重身份,即相对于其他工人,他们是剥削工人的剥削者;相对于资本家,他们又是被剥削的劳动者。其实,马克思的本意是,在本质上总是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并不存在工人对工人的剥削,而在外在现象和形式上则“表现为”工人对工人的剥削。在此,现象关系是以歪曲或颠倒的形式表现和反映本质关系的,或者说,资本剥削劳动的本质是通过劳动剥削劳动这一假象来实现自己或为自己开辟道路的。又如,在《共产党宣言》中,针对资产阶级思想家的责难,马克思和恩格斯作了如下回应:“你们是责备我们要消灭父母对子女的剥削吗?我们承认这种罪状。”[20](P290)如若不进行深入研究,就会误以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承认在家庭关系中,即在父母与子女之间也存在着经济剥削,从而片面扩大马克思的剥削范畴的外延。我们注意到,这种情况和问题也出现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指出:“贫困堕落的双亲只想从孩子身上榨取尽可能多的东西。孩子们长大以后,自然也就对他们的双亲漠不关心并弃之不管了。”[10](P540)不过,马克思对此的解释是:“不是亲权的滥用造成了资本对未成熟劳动力的直接或间接的剥削,相反,正是资本主义的剥削方式通过消灭与亲权相适应的经济基础,造成了亲权的滥用。”[10](P563)就是说,决不能离开经济关系和经济基础去抽象地看待家庭关系和亲权关系,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剥削关系势必会对工人家庭的亲权关系产生影响,从而使后者发生扭曲和畸变。以此来看,父母对子女的榨取只是外在形式或表面现象,它不过是资本实现对劳动剥削的一种具体形式,因而在本质上仍然是资本对劳动的剥削。因此,并不存在父母对子女的所谓“家庭剥削”,一如不存在劳动者(工人)对劳动者(工人)的剥削。
另一方面,马克思一些看似自相矛盾的论述,只有通过深入研究才能疏通和理顺,才能真正弄清就里。例如,针对庸俗经济三位一体的收入分配公式,马克思指出:“由每年新追加的劳动新加进的价值,——从而,年产品中体现这个价值并且能够从总收益中取出和分离出来的部分,——分成三个部分,它们采取三种不同的收入形式,这些形式表明,这个价值的一部分属于或归于劳动力的所有者,另一部分属于或归于资本的所有者,第三部分属于或归于地产的所有者。因此,这就是分配的关系或形式,因为它们表示出新生产的总价值在不同生产要素的所有者中间进行分配的关系。”[7](P993)在此,马克思似乎承认“资本”是与“地产”和“劳动力”并列的生产要素,若果真如此,就与前述马克思关于资本不是生产要素的论断发生冲突。又如,马克思提出:“商品价值的各个组成部分是作为独立的收入互相对立的,并且它们作为独立的收入,是与劳动、资本和土地这三种彼此完全不同的生产要素发生关系,因而好像它们就是由这些东西产生的。”[7](P982)这一段论述似乎比上一段更为明确地肯定了资本是一种生产要素。实际上,只要认真研究一番就会明白,马克思在此是在转述资产阶级经济家的错误观点,而非正面陈述自己的理论主张。因为,把劳动、资本和土地看成三个并列的生产要素,是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家和庸俗经济家的共同理论主张,之后的资产阶级新古典经济又把技术和管理等加入生产要素中来。对马克思而言,不仅资本不是生产要素,而且一般意义上的土地也不是生产要素。作为生产要素,土地必须转化为劳动资料或劳动对象,即必须转化为生产资料。对于资本和生产要素的关系,马克思认为:“只是由于劳动采取雇佣劳动的形式,生产资料采取资本的形式这样的前提,——也就是说,只是由于这两个基本的生产要素采取这种独特的社会形式,——价值(产品)的一部分才表现为剩余价值,这个剩余价值才表现为利润(地租),表现为资本家的赢利,表现为可供支配的、归他所有的追加的财富。”[7](P998)可见,如果说雇佣劳动是劳动力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所采取的一种社会形式,那么,资本就是生产资料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所采取的一种社会形式。生产资料只是资本的物质载体,资本和资本的载体是两种性质不同的东西,不能混为一谈。如上所述,生产要素体现的是“技术关系”,或者说是物在技术关系中所获得的规定,而资本在本质上则是一种“权力—支配关系”,二者具有本质的区别,断不可混为一谈。
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是既成不变的,而是需要与时俱进的,即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发展;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和立场是不变的,变化的总是对把本质和规律与现象连接起来的中介环节和中介过程的具体分析,总是对由此决定的本质和规律的表现形式和实现方式的具体分析。一些人借口时代的变迁,如物质劳动向所谓“非物质劳动”或“生命政治劳动”的转化,数字劳动和平台经济的发生和发展等,否定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和剥削理论的当代性,认为马克思思想已经跟不上时代了,已经过时了。要回应这种观点,就需要结合时代变迁中出现的新情况、新特点和新问题,对马克思思想进行新的学习、新的研究和新的阐释。
只有立足于学术研究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课,才能形成自己的风格特色,才能彰显自身的理论个性与魅力。要成为合格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课教师,必须经过严格而规范的学术训练和培养,经过系统而深入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和研究,否则难以基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把握和回答重大问题,更难以回应和回击向马克思主义理论发起的种种攻讦和挑战,其教学的针对性和有效性也是可想而知的。
参考文献:
[1]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3]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N].人民日报,2021-12-11(1).
[4]习近平.思政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J].求是,2020,(17).
[5][英]琼,罗宾逊.经济哲学[M].安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
[6]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
[7]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8]Marx K. Das Kapital[M].Dritter Band, Berlin: Dietz Verlag, 1966.
[9]Marx K. Capital, Vol.Ⅲ[M].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67.
[10]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11]Marx K. Das Kapital[M].Erster Band, Berlin: Dietz Verlag, 1968.
[12]MarxK.Capital, Vol.Ⅰ[M].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67.
[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4]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1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1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17][英]米克.劳动价值学说的研究[M].陈彪如,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
[1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1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2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