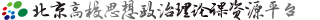【摘要】厘清“思想政治理论课获得感”的科学内涵,是对思想政治理论课获得感进行学理研究的逻辑前提。目前学界主要从词根词源角度以及与西方热词比较角度,对获得感及思想政治教育获得感做了初步研究。对“思想政治理论课获得感”的界定不能简单照搬“思想政治教育获得感”的概念。在综合考虑思想政治理论课获得感的德育课程性质,思想政治理论课获得感的结构层次,思想政治理论课获得感主体对象的基础上,思想政治理论课获得感主要指全体大学生也包括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通过单独的或系统的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学与教,取得知识论层面的、价值观层面的和方法论层面的实际增益和主观受益的统称。
【关键词】思想政治理论课;获得感;《总体方案》
【作者简介】姚迎春(1977-),女,湖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湖北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湖北大学分中心硕士生导师;杨业华(1963-),男,湖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湖北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湖北大学分中心博士生导师(湖北武汉430062)。
【原文出处】《湖北社会科学》(武汉),2018.4.183~187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课题“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14ZDA008)子课题阶段性成果。
自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次会议上,首次提出“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以来,“获得感”迅速成为一个理论热词被广泛使用。2017年5月教育部党组审议通过的《2017年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质量年专项工作总体方案》(以下简称《总体方案》)也提出,2017年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质量年”,要打一场提高高校思想政治课质量和水平的攻坚战,大力提升学生对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获得感。
《总体方案》中强调的“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获得感”,既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意识形态领域工作和思想政治工作系列讲话精神的呼应,也是从思想政治理论课“主阵地”层面对“获得感”问题的照应,还是对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实际中“获得感不足”这一“现实问题”的回应。厘清“思想政治理论课获得感”的科学内涵,是对思想政治理论课获得感进行学理研究的逻辑前提。
一、思想政治理论课获得感内涵的研究现状
“思想政治理论课获得感”由“思想政治理论课”和“获得感”联合构成。鉴于“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内涵已相对明确,在此分别就“获得感”和“思想政治理论课获得感”内涵的研究状况予以梳理。
(一)“获得感”内涵的研究状况
1.从词根词源角度。这种研究思路一般是:先分别解释什么是“获得”,什么是“感”,进而分析“获得”与“获得感”的关系。程仕波和熊建生根据《现代汉语大词典》对“获得”的解释——获得是指取得,得到(多用于抽象事物),指出思想政治教育获得包括两种形式,一种是主动的获得,一种是教育对象被动接受与等待教育者的给予内容。思想政治教育获得感是教育者“供给”与教育对象“求取”双边互动中产生的主观体验。[1]他们重在强调思想政治教育获得过程是主动、动态的抓取过程和被动、静态的接受过程的辩证统一。张品根据《现代汉语大词典》对“获得”词条的解释指出,“获得”本身就包括显性和隐性两个方面,既有物质方面看得见的得到,也有精神层面看不见的得到。他还指出,无论是《说文解字》还是《现代汉语词典》以及对应的英文词汇“obtained sense”,对“感”的解释都与人的主观意愿、精神层面联系密切。因此,他认为“获得感”追求的是“获得”,着眼点是“感”,“获得感”是指因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的获得而产生的可以长久维持下来的满足感,它强调在为我的基础上的一种实实在在的得到。[2]这种解释认为获得感包括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强调“获得感”的持久性和实在性。杨伟基和张方玉指出,获得是增加“获得感”的前提,却不是“获得感”的关键,因为获得感虽然是以实际获得为基础,但并不是等量的,有时甚至不是正相关的,“意义获得感”与“实在获得感”共同构成了“获得感”的完整内容。[3]这种解释突出了“感”的主观性,强调了“意义获得感”的“重要意义”。宋晓岩还从构词方式角度分析了“获得感”成为年度流行语的原因。[4]可见,目前从词根词源词义的角度,关于“获得感”至少在以下方面达成了初步共识:(1)“获得感”是一个典型的附加法构词,由词根“获得”加上类后缀“感”构成。但是后缀的“感”不可虚化,“获得感”追求的是“获得”,着眼点是“感”;(2)要从多维角度理解“获得感”,“获得感”是客观与主观、显性与隐性、物质与精神、静态与动态的辩证统一。
2.从西方学术语境中相近词汇的比较角度。曹现强指出,“获得感”是一个本土性非常强的“中国概念”,在国外尚不存在直接的对应概念。它与国外社会治理中的一些热门概念如“幸福感”“主观生活质量”等,存在一定的相似性,但这些概念往往更偏重于主观感知,且在评价主体、评价内容与评价标准等方面与“获得感”存在一定的区别。他进一步区分“获得感”和“幸福感”,指出“同样是主观感受,‘获得感’和‘幸福感’可以有很多共通之处,但‘幸福感’往往更强调个体心理感受、更主观因此也更容易流于空泛,‘获得感’则更强调‘实惠’,更具体也更有实际意义。同时,‘获得感’不仅是对于‘绝对获得’的感觉,还由所‘相对获得’决定……”因此,获得感内在地包含了两个特征:首先,“获得感”不是个别人的获得感,而是“所有人”的获得感,它必须具有公平公正的特征,保证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能够公平、公正地共享发展成果;其次,弱势群体、边缘群体的“获得感”格外重要,“获得感”必须具有包容性的特征。[5]这种解释充分考虑了“获得感”提出的时代背景,突出了“获得感”的“民生”和“公平”导向。张品指出,“获得感”的提出旨在消除群众特别是弱势群体心中的“失落感”。[2]就我国目前来说,“获得感”多指人民群众共享改革成果的幸福指数,而幸福指数可以通过许多具体方面表现出来。获得感是一种实在的得到,相比于幸福感,它更加务实并且更加贴近现实需要。幸福感则给人一种高远、缥缈的感觉,相比之下也显得相对空泛。因此,“获得感”比幸福感的实现更加具有可衡量行的指标。
(二)思想政治理论课获得感内涵的研究状况
关于思想政治理论课获得感,目前直接研究该问题的论文涉及思想政治理论课获得感重要意义、逻辑生成及教学改革等方面,但均未对其内涵做出明确界定。
笔者检索到的论文中,《论思想政治教育获得感》一文对“思想政治教育获得感”的界定与本文核心概念最为接近:“我们尝试着对其进行界定并认为,思想政治教育获得感意指教育对象对自身在接受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中或过程后获得的精神利益及其对该获得内容的积极主观体验。从内容的维度,思想政治教育获得感得以产生的内容包括两个方面:思想政治教育本身所蕴含的内容和不同的教育对象对思想政治教育的预期内容;从时空维度,思想政治教育获得感包含对以往获得的回忆,对当下收获的体悟,对未来收获的信心”。[1]
此文将思想政治教育的“获得感”视为实际所获(主要是精神利益层面)+主观体验(积极性质的),且分析了思想政治教育获得感变动所关涉的两个变量——实际获得与心理需求之间的多重组合关系。作者遵循从过程到结果的逻辑维度、从过去—当下—未来的时空维度考察思想政治教育获得感,这种思路对我们界定“思想政治理论课获得感”不无启示。但我们也要认识到“思想政治理论课获得感”相比于“思想政治教育获得感”,是一个更加具体的角度,具有鲜明的课程性质,因此不能照搬“思想政治教育获得感”的概念。
二、界定思想政治理论课获得感的思考维度
我们要界定思想政治理论课获得感“是什么”,首先应当思考:当我们在谈论“思想政治理论课获得感”时,我们是将其放在什么样的视阈和维度,它和一般意义上的“获得感”有何不同?
(一)要考虑思想政治理论课获得感的德育课程性质
党的十八大以来,学界对“获得感”的研究大都是围绕“全面深化改革”和“正风反腐”这两大背景和主题而展开的。这种视角从宏观和整体出发,是针对部分群众特别是弱势群体因为不能充分共享改革成果而缺少“获得感”,担心腐败问题若不能有效遏制将会降低人民群众的“获得感”。这种层面上“获得感”的反义词是“失落感”“相对剥夺感”。
我们讨论的思想政治理论课获得感,虽然离不开“全面深化改革”和“正风反腐”这一宏观的社会语境和政治生态背景,但它更多的是从思想政治理论课“主阵地”“主渠道”这一中观层面出发的。我们要在课程论的分析框架中探讨“思想政治理论课获得感”,并要考虑其作为德育课程的特殊性。
被称为“现代课程理论之父”的泰勒提出了著名的“泰勒原理”,即这四个基本问题——确定教育目标、选择教育经验(学习经验)、组织教育经验、评价教育经验,是开发任何课程和教学计划都必须回答的基本问题。泰勒模式中教育目标确立的来源有三——学生、社会和学科。在“思想政治理论课获得感”概念之前,我们讨论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有效性”“思想政治理论课满意度”等概念,更多的是从学科理论分析框架、从社会本位要求的角度出发思考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效果问题。而“获得感”这个概念无疑更加突出了泰勒模式中目标确立三大来源之一的“学生”这一主体端。
泰勒理论中“学习经验”概念对于我们理解“思想政治理论课获得感”也有启发。“‘学习经验’(learning experience)这个术语,不等同于一门课程所涉及的内容,也不等同于教师所从事的各种活动。‘学习经验’是指学习者与他对做出反应的环境中的外部条件之间的相互作用。学习是通过学生的主动行为而发生的,学生的学习取决于他自己做了些什么,而不是教师做了些什么。”[6](p49)泰勒还提出了学习经验的两种组织即“纵向组织”(指不同阶段的学习经验之间的联系)和“横向组织”(指不同领域的学习经验的联系),而有效组织学习经验有三个标准,即“连续性”(直线式地重复主要的课程要素),“序列性”(强调后续经验建立在先前经验的基础的同时又对有关问题进行更广泛,更深入的探讨),“整合性”(指课程经验之间的横向联系)。这些理论可以帮助我们解释和解决“为什么同一课堂上学生的获得感差别大”的问题,也启示我们讨论大学生对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获得感时,要充分考虑大学生“主动取得”的重要性,也提醒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要注意所授课程与中学政治课之间的有机衔接,要关注所带学生高中阶段文科、理科的不同背景,要留心所教课程与学生专业课程之间的差异与融合,还要关注学生以往价值经验和学习态度对思想政治理论课学习的“先入”效应等。
除从一般的课程论角度进行思考,我们尤其还要考虑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德育性质。专业课主要解决学生“知”与“不知”的问题,而思想政治理论课则重在解决学生“信与不信”“行与不行”的问题。思想政治理论课获得感与专业课获得感相比,其内容结构、表现形态、呈现方式、评价标准等均有明显不同,具有鲜明的隐蔽性、模糊性、滞后性、困难性等特征。所以,我们在讨论思想政治理论课获得感时,一定要考虑其课程性质的特殊性,不能将其获得感与专业类课程获得感简单类比或直接搬用。
(二)要考虑思想政治理论课获得感的结构层次
为了深刻理解“思想政治理论课获得感”内涵,一方面我们要“横向”深入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体系内部,既考察大学生对思想政治理论课中每门课程的获得感,也考察大学生从整体意义上对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获得感;另一方面我们要“纵向”切入思想政治理论课获得感的内容结构中,分析思想政治理论课获得感到底是指哪些内容,这些内容之间有何关系等。
思想政治理论课是一个有机的课程体系,其中每一类和每一门课在获得感“供给”方面都各有侧重与特点。例如,必修课中的“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以“适应大学新生活”开篇,比较契合新生的实际需求,学生学习此章节时获得感通常较为直接和明显;随着后续章节理想信念、道德素质、法律素养、人生修养等内容的层层递进,大学生的获得感也会变得相对抽象和隐蔽,但事实上,后面部分能够“供给”的获得感更加深刻和长远。这就要求任课教师上课要力争“生活上的指导和思想上的引导”相结合,即做到所谓的“有虚有实”。又如,“形势与政策”课一般由领导或专家结合时事热点进行专题讲座,提供的“获得感”往往更具即时性和集中性等特点;实践课时“供给”的“获得感”则更具直观性和体验性等。因此,我们谈论“思想政治理论课获得感”时,一方面要将“思想政治理论课”这一课程体系掰开来,具体地分析每一类、每一门课程在“获得感”的供给、需求和生成等方面的特点。另一方面,要将这些课程当成一个有机整体合起来,综合考虑它们作为“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获得感。
思想政治理论课“获得感”的内容也具一定的层次性。我们不能简单地将“获得感”作为一个统称来谈论,还需结合其特殊课程性质来具体剖析“获得感”内容层次。目前学界对此研究不多,笔者认为,“思想政治理论课获得感”虽然形式多样内容庞杂,但按照其作用于大学生素质结构的层面来划分,主要包括以下三大板块的主体内容,它们分别是:1.知识论层面的获得感。思想政治理论课是德育课程当然以“育德”为主,但“益智”也是其内在之意。大学生对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获得感,自然而然地也应包括知识上的进益。当然,思想政治理论课所传授的“知识”与其他专业课的“知识”相比,并不是那么地“专”和“细”,而是围绕着“育德”这一目标的跨学科知识重组,具有强烈的跨学科性和基础性。2.价值观层面的获得感。思想政治理论课说到底是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三观”的课程,大学生在价值观层面的获益是最核心的获得感。不同的思想政治理论课分别从各个侧面切近不同维度的价值观问题,但整类课程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线串联起来,最终落脚到增进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3.方法论层面的获得感。大学生对思想政治理论课获得感的最高表现为方法论层面的获得感。大学生通过思想政治理论课,不仅可以取得人际关系适应、心理健康维护等具体方法上的收获,更重要的是从思维方式和思考方法上有根本性的提升。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课,能帮助大学生从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高度,学习运用辩证的、系统的思维方法思考人生和解决问题。
(三)要考虑思想政治理论课获得感的主体对象
《总体方案》强调“提高大学生对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获得感”,但是将其视为一个严谨的学理概念,我们还可进一步思考,“思想政治理论课获得感”是不是单指大学生的获得感?这里的“大学生”是指全体大学生还是部分大学生?
1.思想政治理论课获得感主要是指大学生的获得感,但也应当包含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获得感。获得感要处理好“给”与“得”的关系,在教学论层面,获得感就是要处理好教与学的关系。思想政治课教师的“给予”是大学生获得感的重要源泉,大学生从思想政治理论课中的“获得”是任课教师获得感的生成动力。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曾强调,要“增强他们(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荣誉感、责任感、获得感”,这当然也包括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获得感。2017年12月教育部印发《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质量提升工程实施纲要》,其中第三条原则“坚持问题导向,注重精准施策”中,明确提出“着力破解高校思想政治工作领域存在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不断提高师生的获得感”。可见,官方话语体系一直是从教师与学生两类主体谈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获得感问题。然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获得感问题”在理论研究中尚未得到足够重视,在媒体镜头和大众话语中还没得到关注,甚至连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群体自身对该问题也无强烈的理论自觉。因此,我们思考思想政治理论课获得感,不应忽视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获得感这一问题。
2.提高大学生对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获得感,是指全体大学生,但要重点关注大学生中的特殊群体和弱势群体。教育部从战略意义上将2017年定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质量年”,也从整体和全局意义上强调“提高大学生对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获得感”,显而易见,这是强调要普遍地提高全体大学生对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获得感。但我们还要看到,“大学生”群体是分层的,大学生对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获得感也是有分别和分化的。我们在思考整体提高大学生对思想政治理论课获得感时,一定要重点关注一些“弱势大学生”的获得感问题。这些大学生中的“弱势群体”,其“弱势”可能来自他所处的非重点院校、边缘专业或偏远地区,也可能来自他所生长的特殊化家庭(例如,贫困家庭、单亲家庭、特定宗教信仰家庭、服刑人员家庭等),还可能来自他自身“弱势”的学习态度和学习能力等。
三、思想政治理论课获得感的初步定义
综前所析,笔者试着给“思想政治理论课获得感”初步下个定义:思想政治理论课获得感,主要指全体大学生也包括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通过单独的或系统的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学与教,取得知识论层面的、价值观层面的和方法论层面的实际增益和主观受益的统称。具体来看,这个定义至少包含以下几层意思:
1.思想政治理论课获得感的主体主要是指全体大学生但也不可忽视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强调“大学生”这一主体,是基于思想政治理论课获得感的生成过程本身就是大学生发挥自身主体能动性的过程,大学生既是思想政治理论课获得感的受益者和评价者,更是思想政治理论课获得感的创造者和合作者;突出“全体”二字,是因为“获得感”一词本身具有公平性和包容性的特征,我们既要从“面”上还要从“层”上考虑大学生对思想政治理论课获得感,尤其要考虑一些弱势大学生群体的获得感问题;不可忽视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获得感,是因为教师只有在“给予”的过程中也“输入获得感”,他才能持续不断地高质量地“输出获得感”。
2.大学生对思想政治理论课获得感主要指整体意义上的获得感但也要重视各类各门课程的获得感。《总体方案》强调“提高大学生对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获得感”,更多是从整体上强调大学生学完这一类课程后的总体获得。总体获得虽然来源于对各类各门课程的具体获得,但又并非将各门课程获得感机械相加的总和。它还涉及各门课程获得感之间的有机衔接、互补和递进等。因此,如何发挥各类各门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特色,如何整合几类几门课“整体育人”的优势,是“提高大学生对思想政治理论课获得感”理应考虑的一个问题。
3.思想政治理论课获得感的内容是一个层层递进的有机体系。大学生从思想政治理论课中获得什么?概括起来说,是一个以知识论层面的获得感为基础,以价值观层面的获得感为核心,以方法论层面的获得感为关键的紧密相连、层层递进的内容体系。这些不同层面的获得感各有不同的呈现方式和特征。例如,知识论层面的获得感具有客观性和确定性等特征,价值观层面的获得感具有即时性与延时性并存的特征,方法论层面的获得感具有隐蔽性和滞后性等特征。因此,当我们谈论大学生对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获得感,我们还要分析是指具体层面的获得感还是总体意义上的获得感,是显性层面的获得感还是隐性层面的获得感,是短效意义上的获得感还是长效意义上的获得感,等等。
4.思想政治理论课获得感的最终大小是一个客观获得和主观感受的相对变量。获得感虽然以实际获得为基础,但它们并不等量,有时甚至不是正相关。思想政治教育获得感是教育者“供给”与教育对象“求取”双边互动中产生的主观体验。[1]这就要求我们在分析思想政治理论课获得感时,一方面要注重教师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教师要将基于社会本位的要求与发自大学生个体本位的需求相结合,将“要求我讲”的内容讲好讲活讲透,讲成学生“希望我讲”的。另一方面也要注重学生的“需求侧结构性改革”,引导大学生从量上和质上确定对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合理需求与目标期待。
以上四层是分别从不同角度对“思想政治理论课获得感”内涵的解释,只有将它们综合起来解读,才能较为完整地理解“思想政治理论课获得感是什么”的问题。
参考文献:
[1]程仕波,熊建生.论思想政治教育获得感[J].思想理论教育,2017,(7).
[2]张品.“获得感”的理论内涵与当代价值[J].河南理工大学学报,2016,(4).
[3]杨伟荣,张方玉.“获得感”的价值彰显[J].重庆社会科学,2016,(11).
[4]宋晓岩.暖心热词:获得感[N].天津日报,2016-01-22.
[5]曹现强.获得感的时代内涵与国外经验借鉴[J].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7,(2).
[6][美]L.W.泰勒.课程与教学的基本原理[M].施良方,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